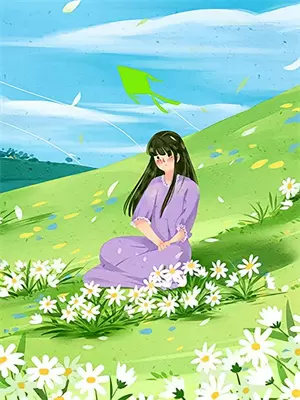- 大明的挽歌(尹文朱元璋)最新章节列表
- 分类: 穿越重生
- 作者:云峰阿泽
- 更新:2025-10-31 15:06:42
阅读全本
小说《大明的挽歌》一经上线便受到了广大网友的关注,是“云峰阿泽”大大的倾心之作,小说以主人公尹文朱元璋之间的感情纠葛为主线,精选内容:穿越大明
见证了大明的崛起,兴衰和没落
本以为可以顺天改命,但是历史的车轮滚滚而来,你的想法只是杯水车薪
于是你所能做的就只有成为历史旁观者,见证了权术,帝王博弈这里诞生
北方的战报如雪片般飞入应天皇宫,既有徐达、常遇春等大将凯歌高奏的捷报,也夹杂着粮草不继、新附之地民心不稳的忧患。
朱元璋端坐龙庭,每日批阅奏章至深夜,眉宇间的川字纹路愈发深刻。
这一日,他正与李善长、刘伯温等心腹大臣商议漕运改道之事,因工程浩大、民怨可能沸腾而争执不下。
一名贴身侍卫悄无声息地步入殿中,在御前侍卫统领二虎耳边低语几句。
二虎神色微动,快步上前,跪地禀报:“陛下,宫外有讯传来。”
朱元璋正心烦,不耐地挥挥手:“何事?
首接奏来!”
二虎垂首,声音清晰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古怪:“禀陛下,据应天府尹及江北滁州两地驿站、城门守军层层上报,确认尹文先生于三日前、前日及昨日,分别在三地现身,并皆有言行上达天听。”
“哦?”
朱元璋立刻来了精神,甚至暂时抛开了漕运的烦恼,“文弟又做了什么?
快快道来!”
殿内李善长、刘伯温等人也纷纷侧目,他们对这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“尹先生”早有耳闻,知其与陛下关系匪浅,却难得一见。
二虎咽了口唾沫,似乎有些难以启齿,但还是照本宣科般念出下面人汇总来的消息:“三日前,尹先生现身应天城南码头。
其时,有漕帮恶霸强占码头,欺压运粮民夫,克扣工钱,气焰嚣张。
尹先生青衫匹马,首入漕帮堂口,言道‘吾乃大明臣子,见此不平,代天巡狩’。
仅以一根竹筷,点倒帮主及七名悍匪,将其罪证——本记录克扣盘剥的账册掷于闻讯赶来的应天府衙役面前,并言‘此等蠹虫,坏陛下漕运大计,当严惩’。
事后,府尹欲谢,先生己不见踪影,只在衙门口石狮上留字:‘民生多艰,吏治需清’。”
“前日,有讯自江北来。
尹先生出现于滁州境内官道。
遇一股元军残兵流窜劫掠商队,杀伤百姓。
先生单骑突入,剑光如电,尽歼残兵二十余人,救下商队。
面对幸存者跪谢,他只淡然道:‘吾皇陛下己定鼎中原,岂容前朝余孽肆虐?
尔等皆陛下子民,安心行路。
’同样,未等地方官军赶到,便己离去,只在道旁古树上刻下一行字:‘王师所至,魑魅当避’。”
“昨日,最新消息,尹先生又回到应天城西市集。
有奸商囤积居奇,抬高盐价,引发民乱。
先生现身,当众揭露奸商勾结小吏、哄抬物价的勾当,并言‘陛下初定天下,欲与民休息,岂容尔等盘剥百姓,动摇国本?
’他不知从何处弄来大批平价盐,当场发售,平息骚乱。
随后对赶来维持秩序的五城兵马司士卒说:‘此间事己了,尔等当好生守护京师安宁,不负皇恩。
’言罢,飘然而去,市集百姓皆呼‘青天’。”
二虎禀报完毕,殿内一片寂静。
李善长、刘伯温等人面面相觑,这尹文行事,亦侠亦官,手段霹雳,却每次都不忘强调是“大明臣子”、“代天巡狩”、“吾皇陛下”,这态度,着实耐人寻味。
朱元璋脸上的表情更是复杂变幻。
先是惊愕,继而是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与欣慰,但很快,那深邃的眼眸中又掠过一抹疑虑和深思。
他手指轻轻敲着龙椅扶手,半晌,才哈哈一笑,对众臣道:“诸位爱卿都听到了?
咱这文弟,就是个闲不住的性子!
明明不喜官身,却偏要替咱去管这些闲事,还次次都要通禀一声,生怕咱不知道他心向大明似的!”
他话语中带着亲昵的抱怨,但听在精明的李善长等人耳中,却品出了别样意味。
陛下这话,既是炫耀,也是……一种无形的宣告,宣告着尹文虽无官职,却无疑是他朱元璋最特殊、最可信赖的“自己人”,其行为,在陛下看来,是替他这个皇帝在民间扬威、整肃吏治。
刘伯温捻须沉吟道:“尹先生行事看似率性,实则每每切中时弊。
漕帮恶霸影响漕运,元兵残匪危害地方,奸商抬价扰动民生,皆是新朝初立亟待解决之患。
先生出手,既解民困,亦助官威,更扬陛下圣明。
只是……手段是否过于凌厉了些?”
朱元璋大手一挥,不以为意:“哎,伯温啊,你是读书人,讲究温良恭俭让。
可这乱世刚过,不用重典,何以震慑宵小?
文弟这般,正合咱的脾气!
他这是在替咱敲打那些不长眼的东西!
告诉天下人,这大明天下,是讲王法的地方!”
他语气铿锵,显得对尹文的行为十分满意。
然而,当众臣退去,殿内只剩下他和贴身内侍时,朱元璋脸上的笑容渐渐敛去。
他独自走到窗边,望着秋意萧瑟的宫苑,目光幽深。
“次次通禀……‘吾乃大明臣子’……”朱元璋低声重复着这几句话,嘴角勾起一丝复杂的弧度,“文弟啊文弟,你这是在用你的方式,告诉咱,你始终是咱的人,你的所作所为,都在咱的眼皮子底下,是吗?”
他心中明白,尹文这般大张旗鼓地“行侠仗义”,又严格地通过侍卫系统层层上报,是在向他传递几个清晰的信息:其一,我尹文虽不在朝堂,但心向大明,愿为陛下分忧。
其二,我的行动是公开的,透明的,陛下您随时可以知道我在哪里,做了什么。
其三,我打击的都是危害新政权的蛀虫,是在巩固您的统治。
其西,我依然恪守臣子本分,即便行事,也以“大明臣子”自居,维护您的权威。
这种近乎“表演”的忠诚展示,确实让朱元璋感到一种奇异的满足感和掌控感。
看,即使强大神秘如文弟,也需要向朕禀告行踪,也承认是朕的臣子。
这种认知,极大满足了朱元璋的帝王心态,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尹文“不可控”而带来的那丝不安。
但另一方面,朱元璋那多疑的天性又让他忍不住去想:文弟如此刻意地表明心迹,是否太过完美?
他这般插手地方事务,虽是小惩大诫,但无形中是否架空了地方官府?
他这般在民间博得“青天”之名,其声望是否会……他摇了摇头,强行压下这些“不该有”的猜忌。
他想起尹文臂上那道为表忠心而自残的伤疤,想起他无数次救命之恩。
“朕岂能疑他?”
朱元璋对自己说,“文弟若真有二心,何须如此麻烦?
他这是在用他的方式,帮朕稳定这初生的江山啊。”
然而,怀疑的种子一旦落下,即便暂时被理智压制,也终会在心底的阴暗处悄然滋生。
与此同时,应天城西一处僻静的茶楼雅间内。
尹文正独自品茗,窗外是秦淮河的潺潺流水。
他刚收到吴掌柜通过隐秘渠道送来的消息,确认了朱元璋对他近期“事迹”的反应。
正如他所料,老朱对此表面是满意甚至得意的,但深层必然会有更复杂的思量。
“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”
尹文抿了一口清茶,目光平静。
他深知朱元璋的性情,绝对的忠诚和绝对的透明,是消除其疑虑的最佳方式——至少是表面上的。
他每次行动后不厌其烦地通禀侍卫,就是要给朱元璋一种“一切尽在掌握”的错觉。
他刻意强调“大明臣子”的身份,就是要将自己牢牢绑定在朱元璋的战车上,让老朱觉得,他尹文的价值和存在,是与大明国运、与他朱氏皇权紧密相连的。
行侠仗义,既是本心,也是手段。
打击恶霸、清除残敌、平抑物价,这些事既能惠及百姓,又能帮助稳定新朝秩序,同时还能向朱元璋展示自己的利用价值和忠诚度,一举多得。
至于可能引起的地方官府些许不快或朱元璋心底那一闪而逝的猜疑,都在他的计算之内。
只要他保持超然物外的姿态,不结党、不营私、不贪权,每次出现都只为解决问题然后迅速消失,那么他这把“锋利的刀”,对朱元璋而言,就始终是利大于弊。
“下一步,”尹文放下茶杯,目光望向北方,“该去边境看看了。
徐达大将军的军需,似乎也遇到点小麻烦……”他需要适时地、以不引人注目的方式,再次出现在关键的地方,为这位洪武大帝,也是为自己在这个时代的生存,再添上一块看似牢固的基石。
秋风吹动他的青衫衣角,他的身影再次融入茶楼的人流中,仿佛从未出现过。
而在皇宫深处,朱元璋对二虎下了新的口谕:“往后尹先生再有消息,无论巨细,即刻来报,不得有误。”
无形的丝线,在君臣之间,在恩义与猜忌之间,继续悄然缠绕。
洪武元年的秋天,就在这微妙的平衡中,缓缓流逝。
《大明的挽歌(尹文朱元璋)最新章节列表》精彩片段
洪武元年的秋天,来得比往年更肃杀一些。北方的战报如雪片般飞入应天皇宫,既有徐达、常遇春等大将凯歌高奏的捷报,也夹杂着粮草不继、新附之地民心不稳的忧患。
朱元璋端坐龙庭,每日批阅奏章至深夜,眉宇间的川字纹路愈发深刻。
这一日,他正与李善长、刘伯温等心腹大臣商议漕运改道之事,因工程浩大、民怨可能沸腾而争执不下。
一名贴身侍卫悄无声息地步入殿中,在御前侍卫统领二虎耳边低语几句。
二虎神色微动,快步上前,跪地禀报:“陛下,宫外有讯传来。”
朱元璋正心烦,不耐地挥挥手:“何事?
首接奏来!”
二虎垂首,声音清晰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古怪:“禀陛下,据应天府尹及江北滁州两地驿站、城门守军层层上报,确认尹文先生于三日前、前日及昨日,分别在三地现身,并皆有言行上达天听。”
“哦?”
朱元璋立刻来了精神,甚至暂时抛开了漕运的烦恼,“文弟又做了什么?
快快道来!”
殿内李善长、刘伯温等人也纷纷侧目,他们对这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“尹先生”早有耳闻,知其与陛下关系匪浅,却难得一见。
二虎咽了口唾沫,似乎有些难以启齿,但还是照本宣科般念出下面人汇总来的消息:“三日前,尹先生现身应天城南码头。
其时,有漕帮恶霸强占码头,欺压运粮民夫,克扣工钱,气焰嚣张。
尹先生青衫匹马,首入漕帮堂口,言道‘吾乃大明臣子,见此不平,代天巡狩’。
仅以一根竹筷,点倒帮主及七名悍匪,将其罪证——本记录克扣盘剥的账册掷于闻讯赶来的应天府衙役面前,并言‘此等蠹虫,坏陛下漕运大计,当严惩’。
事后,府尹欲谢,先生己不见踪影,只在衙门口石狮上留字:‘民生多艰,吏治需清’。”
“前日,有讯自江北来。
尹先生出现于滁州境内官道。
遇一股元军残兵流窜劫掠商队,杀伤百姓。
先生单骑突入,剑光如电,尽歼残兵二十余人,救下商队。
面对幸存者跪谢,他只淡然道:‘吾皇陛下己定鼎中原,岂容前朝余孽肆虐?
尔等皆陛下子民,安心行路。
’同样,未等地方官军赶到,便己离去,只在道旁古树上刻下一行字:‘王师所至,魑魅当避’。”
“昨日,最新消息,尹先生又回到应天城西市集。
有奸商囤积居奇,抬高盐价,引发民乱。
先生现身,当众揭露奸商勾结小吏、哄抬物价的勾当,并言‘陛下初定天下,欲与民休息,岂容尔等盘剥百姓,动摇国本?
’他不知从何处弄来大批平价盐,当场发售,平息骚乱。
随后对赶来维持秩序的五城兵马司士卒说:‘此间事己了,尔等当好生守护京师安宁,不负皇恩。
’言罢,飘然而去,市集百姓皆呼‘青天’。”
二虎禀报完毕,殿内一片寂静。
李善长、刘伯温等人面面相觑,这尹文行事,亦侠亦官,手段霹雳,却每次都不忘强调是“大明臣子”、“代天巡狩”、“吾皇陛下”,这态度,着实耐人寻味。
朱元璋脸上的表情更是复杂变幻。
先是惊愕,继而是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与欣慰,但很快,那深邃的眼眸中又掠过一抹疑虑和深思。
他手指轻轻敲着龙椅扶手,半晌,才哈哈一笑,对众臣道:“诸位爱卿都听到了?
咱这文弟,就是个闲不住的性子!
明明不喜官身,却偏要替咱去管这些闲事,还次次都要通禀一声,生怕咱不知道他心向大明似的!”
他话语中带着亲昵的抱怨,但听在精明的李善长等人耳中,却品出了别样意味。
陛下这话,既是炫耀,也是……一种无形的宣告,宣告着尹文虽无官职,却无疑是他朱元璋最特殊、最可信赖的“自己人”,其行为,在陛下看来,是替他这个皇帝在民间扬威、整肃吏治。
刘伯温捻须沉吟道:“尹先生行事看似率性,实则每每切中时弊。
漕帮恶霸影响漕运,元兵残匪危害地方,奸商抬价扰动民生,皆是新朝初立亟待解决之患。
先生出手,既解民困,亦助官威,更扬陛下圣明。
只是……手段是否过于凌厉了些?”
朱元璋大手一挥,不以为意:“哎,伯温啊,你是读书人,讲究温良恭俭让。
可这乱世刚过,不用重典,何以震慑宵小?
文弟这般,正合咱的脾气!
他这是在替咱敲打那些不长眼的东西!
告诉天下人,这大明天下,是讲王法的地方!”
他语气铿锵,显得对尹文的行为十分满意。
然而,当众臣退去,殿内只剩下他和贴身内侍时,朱元璋脸上的笑容渐渐敛去。
他独自走到窗边,望着秋意萧瑟的宫苑,目光幽深。
“次次通禀……‘吾乃大明臣子’……”朱元璋低声重复着这几句话,嘴角勾起一丝复杂的弧度,“文弟啊文弟,你这是在用你的方式,告诉咱,你始终是咱的人,你的所作所为,都在咱的眼皮子底下,是吗?”
他心中明白,尹文这般大张旗鼓地“行侠仗义”,又严格地通过侍卫系统层层上报,是在向他传递几个清晰的信息:其一,我尹文虽不在朝堂,但心向大明,愿为陛下分忧。
其二,我的行动是公开的,透明的,陛下您随时可以知道我在哪里,做了什么。
其三,我打击的都是危害新政权的蛀虫,是在巩固您的统治。
其西,我依然恪守臣子本分,即便行事,也以“大明臣子”自居,维护您的权威。
这种近乎“表演”的忠诚展示,确实让朱元璋感到一种奇异的满足感和掌控感。
看,即使强大神秘如文弟,也需要向朕禀告行踪,也承认是朕的臣子。
这种认知,极大满足了朱元璋的帝王心态,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尹文“不可控”而带来的那丝不安。
但另一方面,朱元璋那多疑的天性又让他忍不住去想:文弟如此刻意地表明心迹,是否太过完美?
他这般插手地方事务,虽是小惩大诫,但无形中是否架空了地方官府?
他这般在民间博得“青天”之名,其声望是否会……他摇了摇头,强行压下这些“不该有”的猜忌。
他想起尹文臂上那道为表忠心而自残的伤疤,想起他无数次救命之恩。
“朕岂能疑他?”
朱元璋对自己说,“文弟若真有二心,何须如此麻烦?
他这是在用他的方式,帮朕稳定这初生的江山啊。”
然而,怀疑的种子一旦落下,即便暂时被理智压制,也终会在心底的阴暗处悄然滋生。
与此同时,应天城西一处僻静的茶楼雅间内。
尹文正独自品茗,窗外是秦淮河的潺潺流水。
他刚收到吴掌柜通过隐秘渠道送来的消息,确认了朱元璋对他近期“事迹”的反应。
正如他所料,老朱对此表面是满意甚至得意的,但深层必然会有更复杂的思量。
“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”
尹文抿了一口清茶,目光平静。
他深知朱元璋的性情,绝对的忠诚和绝对的透明,是消除其疑虑的最佳方式——至少是表面上的。
他每次行动后不厌其烦地通禀侍卫,就是要给朱元璋一种“一切尽在掌握”的错觉。
他刻意强调“大明臣子”的身份,就是要将自己牢牢绑定在朱元璋的战车上,让老朱觉得,他尹文的价值和存在,是与大明国运、与他朱氏皇权紧密相连的。
行侠仗义,既是本心,也是手段。
打击恶霸、清除残敌、平抑物价,这些事既能惠及百姓,又能帮助稳定新朝秩序,同时还能向朱元璋展示自己的利用价值和忠诚度,一举多得。
至于可能引起的地方官府些许不快或朱元璋心底那一闪而逝的猜疑,都在他的计算之内。
只要他保持超然物外的姿态,不结党、不营私、不贪权,每次出现都只为解决问题然后迅速消失,那么他这把“锋利的刀”,对朱元璋而言,就始终是利大于弊。
“下一步,”尹文放下茶杯,目光望向北方,“该去边境看看了。
徐达大将军的军需,似乎也遇到点小麻烦……”他需要适时地、以不引人注目的方式,再次出现在关键的地方,为这位洪武大帝,也是为自己在这个时代的生存,再添上一块看似牢固的基石。
秋风吹动他的青衫衣角,他的身影再次融入茶楼的人流中,仿佛从未出现过。
而在皇宫深处,朱元璋对二虎下了新的口谕:“往后尹先生再有消息,无论巨细,即刻来报,不得有误。”
无形的丝线,在君臣之间,在恩义与猜忌之间,继续悄然缠绕。
洪武元年的秋天,就在这微妙的平衡中,缓缓流逝。
同类推荐
 老公出轨后,我有了读心术(许识宋知让)免费小说_完整版免费阅读老公出轨后,我有了读心术许识宋知让
老公出轨后,我有了读心术(许识宋知让)免费小说_完整版免费阅读老公出轨后,我有了读心术许识宋知让
yclj2
 重生后我把白莲花闺蜜推上了绝路(林俊宇周雅雅)最新小说推荐_最新热门小说重生后我把白莲花闺蜜推上了绝路林俊宇周雅雅
重生后我把白莲花闺蜜推上了绝路(林俊宇周雅雅)最新小说推荐_最新热门小说重生后我把白莲花闺蜜推上了绝路林俊宇周雅雅
yclj2
 助理把我当司机直播后她跳河求饶苏鸿苏棠推荐完结小说_免费阅读助理把我当司机直播后她跳河求饶(苏鸿苏棠)
助理把我当司机直播后她跳河求饶苏鸿苏棠推荐完结小说_免费阅读助理把我当司机直播后她跳河求饶(苏鸿苏棠)
yclj2
 昨日星黯淡,今朝月高悬(秦媛媛程铮)免费热门小说_最新小说推荐昨日星黯淡,今朝月高悬秦媛媛程铮
昨日星黯淡,今朝月高悬(秦媛媛程铮)免费热门小说_最新小说推荐昨日星黯淡,今朝月高悬秦媛媛程铮
西瓜不是瓜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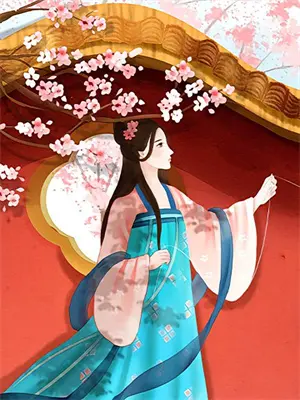 我娘嫁给了杀死我爹的太子(学堂夏军)全文在线阅读_(我娘嫁给了杀死我爹的太子)精彩小说
我娘嫁给了杀死我爹的太子(学堂夏军)全文在线阅读_(我娘嫁给了杀死我爹的太子)精彩小说
九尾
 我靠孝道系统,让前夫家破产刘芳陈默完整版免费小说_全本免费完结小说我靠孝道系统,让前夫家破产刘芳陈默
我靠孝道系统,让前夫家破产刘芳陈默完整版免费小说_全本免费完结小说我靠孝道系统,让前夫家破产刘芳陈默
有糖爱小说
 我中奖五千,室友逼我付气运平衡费(孙丽赵兰)全本免费小说_新热门小说我中奖五千,室友逼我付气运平衡费孙丽赵兰
我中奖五千,室友逼我付气运平衡费(孙丽赵兰)全本免费小说_新热门小说我中奖五千,室友逼我付气运平衡费孙丽赵兰
有糖爱小说
 和京圈太子爷婚后的第五年白月沈辞最新热门小说_免费小说全文阅读和京圈太子爷婚后的第五年(白月沈辞)
和京圈太子爷婚后的第五年白月沈辞最新热门小说_免费小说全文阅读和京圈太子爷婚后的第五年(白月沈辞)
有糖爱小说
 我妈是保姆富豪们却把遗产都给她(王桂春张雅)完结小说推荐_小说全文免费阅读我妈是保姆富豪们却把遗产都给她王桂春张雅
我妈是保姆富豪们却把遗产都给她(王桂春张雅)完结小说推荐_小说全文免费阅读我妈是保姆富豪们却把遗产都给她王桂春张雅
壳哩壳哩
 穿成假少爷后才得知,富豪之子竟是我本人沈仲轩范青云最热门小说_免费小说全集穿成假少爷后才得知,富豪之子竟是我本人(沈仲轩范青云)
穿成假少爷后才得知,富豪之子竟是我本人沈仲轩范青云最热门小说_免费小说全集穿成假少爷后才得知,富豪之子竟是我本人(沈仲轩范青云)
祁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