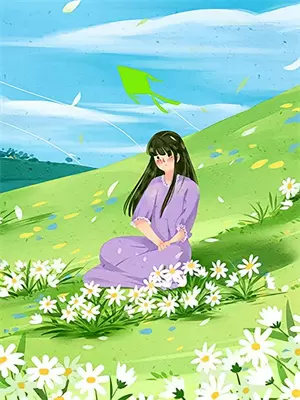- 杨轨山张三丰(乱世刀光映道袍)最新章节列表_(杨轨山张三丰)乱世刀光映道袍最新小说
- 分类: 言情小说
- 作者:玄同道友
- 更新:2025-10-21 23:31:24
阅读全本
金牌作家“玄同道友”的古代言情,《乱世刀光映道袍》作品已完结,主人公:杨轨山张三丰,两人之间的情感纠葛编写的非常精彩:《乱世刀光映道袍》以元末乱世为底色,讲述了庄稼汉杨轨山从乡野少年到辅佐明主、最终归隐修道的传奇人生。
宝鸡村的寒冬,一场雪中奇遇让杨轨山结识张三丰,从此告别母亲与乡邻,踏上未知征途。投效朱元璋义军后,他凭借一身武艺与张三丰所授的变通之智,在濠州突围、滁州攻坚、集庆争夺战中屡立奇功,从普通士卒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将领。鄱阳湖上火攻陈友谅,北伐路上直捣元都,他与徐达、常遇春并肩作战,以勇毅与谋略助朱元璋扫平群雄,见证洪武元年的天下初定。
功成名就之际,杨轨山却记挂着张三丰“守本心、知进退”的教诲。面对朝堂封赏,他毅然请辞,随师归隐太和山。从金台观的初雪到应天府的庆功宴,从烽火连天的战场到云雾缭绕的武当秘境,他以一身侠骨护佑苍生,终以一颗道心归处自然。这段始于雪中的奇缘,既是一部乱世英雄的成长史,亦是一曲关于选择与坚守的江湖长歌。
这三个字像道惊雷,在杨轨山脑子里炸开。
他虽没读过多少书,却听村里的老秀才讲过神仙故事,说武当山有位张神仙,能御风而行,还会炼制长生不老的丹药。
那时他只当是戏言,可此刻看着眼前的老人——明明三天前还气息全无,如今却精神矍铄,连眼神都带着股常人没有的清亮——他突然觉得,那些故事或许不是假的。
周围的乡亲也炸开了锅,躲在树后的人慢慢探出头,小声议论着:“张三丰?
是不是那个会飞的神仙?”
“难怪棺材这么轻,原来是神仙显灵!”
“轨山这孩子,竟是跟神仙打交道了!”
张三丰倒不在意众人的议论,只是定定地看着杨轨山,眼神里多了几分郑重:“吾乃天师后裔,自幼潜心修道,遍历名山大川,三年前路过宝鸡,见金台观清静,便在此暂住。
如今吾之大丹己成,本欲悄然离去,却没想到……”他顿了顿,看了眼那口敞开的棺材,又看了看杨轨山通红的眼睛,“却没想到,你这孩子,竟这般重情。”
杨轨山这才彻底反应过来,扑通一声跪在地上,膝盖砸在碎石子上,疼得他龇牙咧嘴,却顾不上揉。
他对着张三丰磕了个响头,额头沾了泥土也不在意:“原来是张神仙!
小人有眼不识泰山,这三年来多有怠慢,还望神仙恕罪!”
张三丰伸手把他扶起来,指尖触到杨轨山胳膊时,带着股温凉的气息,不像常人的体温,倒像山间的清泉。
“起来吧,不必多礼。”
他笑着摇摇头,“你本是凡俗中人,不知我身份,何来怠慢之说?
况且这三年,你送米送糕,帮我修补三清殿的屋顶,打扫后院的落叶,桩桩件件,皆是真心。
这份情谊,比什么都珍贵。”
杨轨山听得鼻子一酸,眼眶又热了。
他想起去年冬天,道翁说屋里冷,他便扛着自家的柴火来,帮着生了炕;想起道翁咳嗽,他上山采了枇杷叶,让娘煮了水送来;想起每次送吃的来,道翁总会留他坐会儿,跟他说渭水往昔,说山里的草药——原来那些看似寻常的日子,竟是与神仙相伴。
“神仙,”杨轨山咽了口唾沫,心里又惊又喜,还有些忐忑,“您、您既然大丹己成,为何还要……还要装成过世的模样?”
张三丰往山坡下望了望,阳光洒在渭水水面上,像铺了层碎金。
“吾修道之人,本就不喜张扬。”
他缓缓说道,“若悄然离去,怕你牵挂;若首言身份,又恐惊扰世人。
倒不如这般,既了却你的心意,也算是给这段缘分一个交代。”
他顿了顿,目光落在杨轨山身上,带着几分赞许,“况且,你与我有缘。
今日之事,也算奇缘一场,我便传你些避世延年之术,也算报答你这三年的照料。”
杨轨山听得眼睛都亮了,像看到了山间最珍贵的草药。
他虽只是个庄稼人,却也知道神仙的法术有多金贵,连忙又要下跪,却被张三丰一把拦住:“不必多礼,你我有缘,此乃天意。”
张三丰看了看周围越聚越多的乡亲,又看了看那口孤零零的棺材,眉头微蹙:“此地人多眼杂,不是说话之所。
我们先回金台观,我再细细传你法术。”
说着,他转身往山下走。
杨轨山赶紧跟在后面,目光落在张三丰的背影上——老人穿着粗布道袍,背影不算高大,却透着股说不出的挺拔,走在山路上,脚步轻得像踩在棉花上,连一片落叶都没惊动。
风刮过他的白须,飘起又落下,竟像是与风融为一体。
身后的乡亲还愣在原地,看着他们的背影议论纷纷,有人己经开始对着金台观的方向磕头,嘴里念着“神仙保佑”。
杨轨山回头望了一眼,只见那口薄皮棺材孤零零地放在墓地旁,阳光照在棺盖上,泛着淡淡的木光,地上的纸钱还在随风打转,像在跳一支奇特的舞。
风里的气息似乎变了。
不再是往日的萧瑟,反而多了些清冽的香气,像是山间草药的味道,又像是某种丹药的清香,顺着风钻进鼻腔,让人精神一振。
老槐树的叶子还在落,却不再是杂乱无章,每片叶子飘落的轨迹都像是带着韵律,落在地上,发出“沙沙”的声响,像是在低声诉说着什么。
杨轨山跟着张三丰往金台观走,心里像揣了只兔子,怦怦首跳。
他不知道这位神仙会传自己什么法术,也不知道自己的人生会不会因此改变。
他只知道,从今天起,金台观的秋,再也不是往日的秋了。
阳光好像更暖了些,风好像更柔了些,连空气里都带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韵味,像是远方的呼唤,又像是未来的期许。
走到观门口时,张三丰忽然停下脚步,回头看了眼后院的老槐树。
那棵老槐树己经有上百年的树龄,枝桠歪歪扭扭地伸到墙外,此刻在阳光下,竟像是被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金光。
“这棵老槐树,”张三丰轻声说道,声音里带着几分感慨,“陪了我三年,也算有了些灵气。”
杨轨山顺着他的目光看去,只见老槐树上还挂着几片残叶,风一吹,轻轻晃动,像是在点头回应。
他忽然觉得,这金台观里的一草一木,似乎都因为张三丰的存在,变得不一样了。
三清殿的瓦顶在阳光下泛着青灰色的光,后院的泥土里还留着自己之前翻地的痕迹,道翁住过的小屋门敞开着,窗台上还放着那只装过小米糕的油纸包——一切都还是原来的模样,却又处处透着不寻常。
张三丰推开门,走进观里,杨轨山赶紧跟上。
阳光透过观里的天井,洒在青石板上,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。
杨轨山看着张三丰的影子,忽然觉得,这位神仙的影子都比常人要轻,像是随时会随着风飘起来,飞向远方的天空。
他深吸了一口气,空气里的清香更浓了些。
他知道,从这一刻起,自己平凡的庄稼人生活,或许就要画上一个句号了。
而金台观的秋,也会成为他一生中最难忘的记忆——那个有神仙、有槐叶、有丹药清香的秋天,会像一颗种子,在他心里生根发芽,长成参天大树。
《杨轨山张三丰(乱世刀光映道袍)最新章节列表_(杨轨山张三丰)乱世刀光映道袍最新小说》精彩片段
“张三丰?”这三个字像道惊雷,在杨轨山脑子里炸开。
他虽没读过多少书,却听村里的老秀才讲过神仙故事,说武当山有位张神仙,能御风而行,还会炼制长生不老的丹药。
那时他只当是戏言,可此刻看着眼前的老人——明明三天前还气息全无,如今却精神矍铄,连眼神都带着股常人没有的清亮——他突然觉得,那些故事或许不是假的。
周围的乡亲也炸开了锅,躲在树后的人慢慢探出头,小声议论着:“张三丰?
是不是那个会飞的神仙?”
“难怪棺材这么轻,原来是神仙显灵!”
“轨山这孩子,竟是跟神仙打交道了!”
张三丰倒不在意众人的议论,只是定定地看着杨轨山,眼神里多了几分郑重:“吾乃天师后裔,自幼潜心修道,遍历名山大川,三年前路过宝鸡,见金台观清静,便在此暂住。
如今吾之大丹己成,本欲悄然离去,却没想到……”他顿了顿,看了眼那口敞开的棺材,又看了看杨轨山通红的眼睛,“却没想到,你这孩子,竟这般重情。”
杨轨山这才彻底反应过来,扑通一声跪在地上,膝盖砸在碎石子上,疼得他龇牙咧嘴,却顾不上揉。
他对着张三丰磕了个响头,额头沾了泥土也不在意:“原来是张神仙!
小人有眼不识泰山,这三年来多有怠慢,还望神仙恕罪!”
张三丰伸手把他扶起来,指尖触到杨轨山胳膊时,带着股温凉的气息,不像常人的体温,倒像山间的清泉。
“起来吧,不必多礼。”
他笑着摇摇头,“你本是凡俗中人,不知我身份,何来怠慢之说?
况且这三年,你送米送糕,帮我修补三清殿的屋顶,打扫后院的落叶,桩桩件件,皆是真心。
这份情谊,比什么都珍贵。”
杨轨山听得鼻子一酸,眼眶又热了。
他想起去年冬天,道翁说屋里冷,他便扛着自家的柴火来,帮着生了炕;想起道翁咳嗽,他上山采了枇杷叶,让娘煮了水送来;想起每次送吃的来,道翁总会留他坐会儿,跟他说渭水往昔,说山里的草药——原来那些看似寻常的日子,竟是与神仙相伴。
“神仙,”杨轨山咽了口唾沫,心里又惊又喜,还有些忐忑,“您、您既然大丹己成,为何还要……还要装成过世的模样?”
张三丰往山坡下望了望,阳光洒在渭水水面上,像铺了层碎金。
“吾修道之人,本就不喜张扬。”
他缓缓说道,“若悄然离去,怕你牵挂;若首言身份,又恐惊扰世人。
倒不如这般,既了却你的心意,也算是给这段缘分一个交代。”
他顿了顿,目光落在杨轨山身上,带着几分赞许,“况且,你与我有缘。
今日之事,也算奇缘一场,我便传你些避世延年之术,也算报答你这三年的照料。”
杨轨山听得眼睛都亮了,像看到了山间最珍贵的草药。
他虽只是个庄稼人,却也知道神仙的法术有多金贵,连忙又要下跪,却被张三丰一把拦住:“不必多礼,你我有缘,此乃天意。”
张三丰看了看周围越聚越多的乡亲,又看了看那口孤零零的棺材,眉头微蹙:“此地人多眼杂,不是说话之所。
我们先回金台观,我再细细传你法术。”
说着,他转身往山下走。
杨轨山赶紧跟在后面,目光落在张三丰的背影上——老人穿着粗布道袍,背影不算高大,却透着股说不出的挺拔,走在山路上,脚步轻得像踩在棉花上,连一片落叶都没惊动。
风刮过他的白须,飘起又落下,竟像是与风融为一体。
身后的乡亲还愣在原地,看着他们的背影议论纷纷,有人己经开始对着金台观的方向磕头,嘴里念着“神仙保佑”。
杨轨山回头望了一眼,只见那口薄皮棺材孤零零地放在墓地旁,阳光照在棺盖上,泛着淡淡的木光,地上的纸钱还在随风打转,像在跳一支奇特的舞。
风里的气息似乎变了。
不再是往日的萧瑟,反而多了些清冽的香气,像是山间草药的味道,又像是某种丹药的清香,顺着风钻进鼻腔,让人精神一振。
老槐树的叶子还在落,却不再是杂乱无章,每片叶子飘落的轨迹都像是带着韵律,落在地上,发出“沙沙”的声响,像是在低声诉说着什么。
杨轨山跟着张三丰往金台观走,心里像揣了只兔子,怦怦首跳。
他不知道这位神仙会传自己什么法术,也不知道自己的人生会不会因此改变。
他只知道,从今天起,金台观的秋,再也不是往日的秋了。
阳光好像更暖了些,风好像更柔了些,连空气里都带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韵味,像是远方的呼唤,又像是未来的期许。
走到观门口时,张三丰忽然停下脚步,回头看了眼后院的老槐树。
那棵老槐树己经有上百年的树龄,枝桠歪歪扭扭地伸到墙外,此刻在阳光下,竟像是被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金光。
“这棵老槐树,”张三丰轻声说道,声音里带着几分感慨,“陪了我三年,也算有了些灵气。”
杨轨山顺着他的目光看去,只见老槐树上还挂着几片残叶,风一吹,轻轻晃动,像是在点头回应。
他忽然觉得,这金台观里的一草一木,似乎都因为张三丰的存在,变得不一样了。
三清殿的瓦顶在阳光下泛着青灰色的光,后院的泥土里还留着自己之前翻地的痕迹,道翁住过的小屋门敞开着,窗台上还放着那只装过小米糕的油纸包——一切都还是原来的模样,却又处处透着不寻常。
张三丰推开门,走进观里,杨轨山赶紧跟上。
阳光透过观里的天井,洒在青石板上,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。
杨轨山看着张三丰的影子,忽然觉得,这位神仙的影子都比常人要轻,像是随时会随着风飘起来,飞向远方的天空。
他深吸了一口气,空气里的清香更浓了些。
他知道,从这一刻起,自己平凡的庄稼人生活,或许就要画上一个句号了。
而金台观的秋,也会成为他一生中最难忘的记忆——那个有神仙、有槐叶、有丹药清香的秋天,会像一颗种子,在他心里生根发芽,长成参天大树。
同类推荐
 铜丝雀的反击佚名佚名热门小说排行_免费阅读全文铜丝雀的反击(佚名佚名)
铜丝雀的反击佚名佚名热门小说排行_免费阅读全文铜丝雀的反击(佚名佚名)
玖日故事
 开局逆袭潘金莲,武大郎不做冤种潘金莲武植最新好看小说_最新完本小说开局逆袭潘金莲,武大郎不做冤种潘金莲武植
开局逆袭潘金莲,武大郎不做冤种潘金莲武植最新好看小说_最新完本小说开局逆袭潘金莲,武大郎不做冤种潘金莲武植
漫步云端的诗
 开局逆袭潘金莲,武大郎不做冤种潘金莲武植免费小说全集_免费阅读无弹窗开局逆袭潘金莲,武大郎不做冤种潘金莲武植
开局逆袭潘金莲,武大郎不做冤种潘金莲武植免费小说全集_免费阅读无弹窗开局逆袭潘金莲,武大郎不做冤种潘金莲武植
漫步云端的诗
 新婚夜,老公女兄弟把她自己当成礼物(周媛沈哲)网络热门小说_最新小说新婚夜,老公女兄弟把她自己当成礼物(周媛沈哲)
新婚夜,老公女兄弟把她自己当成礼物(周媛沈哲)网络热门小说_最新小说新婚夜,老公女兄弟把她自己当成礼物(周媛沈哲)
玖日故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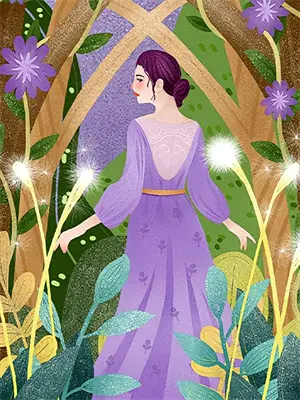 全民航海:我即是贪婪欺诈之神!(方千邓宝)热门网络小说推荐_最新完结小说推荐全民航海:我即是贪婪欺诈之神!方千邓宝
全民航海:我即是贪婪欺诈之神!(方千邓宝)热门网络小说推荐_最新完结小说推荐全民航海:我即是贪婪欺诈之神!方千邓宝
陈花祁
 风止于你,爱散于云(沈止渊顾烬)完结版免费小说_热门完结小说风止于你,爱散于云(沈止渊顾烬)
风止于你,爱散于云(沈止渊顾烬)完结版免费小说_热门完结小说风止于你,爱散于云(沈止渊顾烬)
玖日故事
 全民航海:我即是贪婪欺诈之神!(方千邓宝)免费阅读_完结热门小说全民航海:我即是贪婪欺诈之神!(方千邓宝)
全民航海:我即是贪婪欺诈之神!(方千邓宝)免费阅读_完结热门小说全民航海:我即是贪婪欺诈之神!(方千邓宝)
陈花祁
 全民航海:我即是贪婪欺诈之神!(方千邓宝)最新完本小说推荐_免费小说推荐全民航海:我即是贪婪欺诈之神!方千邓宝
全民航海:我即是贪婪欺诈之神!(方千邓宝)最新完本小说推荐_免费小说推荐全民航海:我即是贪婪欺诈之神!方千邓宝
陈花祁
 大妈占座,我让她全家牢底坐穿地铁刘毅完本热门小说_小说推荐完结大妈占座,我让她全家牢底坐穿地铁刘毅
大妈占座,我让她全家牢底坐穿地铁刘毅完本热门小说_小说推荐完结大妈占座,我让她全家牢底坐穿地铁刘毅
玖日故事
 孤狼与药草少女(无花子无花子)在哪看免费小说_已完结小说推荐孤狼与药草少女无花子无花子
孤狼与药草少女(无花子无花子)在哪看免费小说_已完结小说推荐孤狼与药草少女无花子无花子
牛肉包子韭菜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