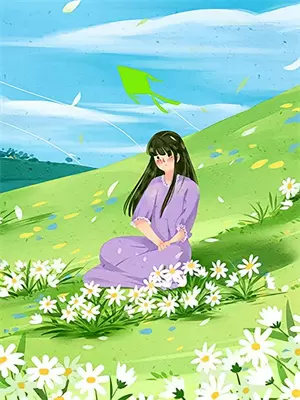- 季风吹过白墙林知夏陈砚知全本免费在线阅读_林知夏陈砚知全文阅读
- 分类: 言情小说
- 作者:一个人的書
- 更新:2025-10-18 08:25:33
《季风吹过白墙林知夏陈砚知全本免费在线阅读_林知夏陈砚知全文阅读》精彩片段
九月的燕园总裹着层薄纱似的桂香,西门外的车流声被浓密的悬铃木滤过,飘进数学系图书馆时只剩细碎的嗡鸣。林知夏把帆布包往阅览区第三排的老位置一放,金属搭扣撞在实木桌面上,发出清脆的声响,惊飞了窗台上蜷着的麻雀。
她今天穿了件米白色针织开衫,袖口卷到小臂,露出腕骨处淡青色的血管。摊开《数学分析习题集》时,指腹蹭过扉页上自己去年写的批注——“连续不代表可导,如同相爱不代表合适”,笔尖顿了顿,又在旁边补了行小字:“但反之是否成立?待证。”
图书馆的落地钟刚敲过九点,斜前方的座位忽然传来拉动椅子的声音。林知夏抬眼的瞬间,撞进一双深褐色的眼睛里。男人穿着深灰色衬衫,袖口严谨地扣到手腕,左手无名指上戴着枚银质素圈戒指,正把笔记本电脑轻放在桌面上。他的动作很轻,却让林知夏的心跳漏了半拍——不是因为对方挺拔的身形,而是他电脑屏幕亮起时,她清晰地看到桌面背景是黎曼猜想的推演公式,和她手机壁纸一模一样。
“抱歉,打扰了。”男人察觉到她的目光,指尖在键盘上悬停片刻,轻声开口。他的声音像秋雨打在青石板上,带着种温润的质感,“这里平时有人吗?”
林知夏摇头时,发梢扫过脸颊:“没有,随便坐。”说完又低下头,假装演算习题,余光却忍不住往那边飘。男人打开的文档标题是《非交换代数在量子计算中的应用》,字体是标准的Times New Roman,段落间距精确到0.5倍行距——和她写论文时的习惯分毫不差。
十点零三分,图书馆的中央空调突然出了故障,送风口开始断断续续地吹热风。林知夏额角渗出细汗,烦躁地把刘海别到耳后,手里的笔在草稿纸上反复画着同一个错误的积分符号。忽然,一片阴影覆在她的习题册上,男人递过来一张纸巾,包装纸上印着北大出版社的logo。
“积分变量换错了。”他指了指她画错的地方,指尖干净修长,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,“这里应该用分部积分,不是变量代换。”
林知夏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,脸颊瞬间发烫。作为数学系直博三年级的学生,犯这种低级错误简直像医生拿反了手术刀。她接过纸巾时,指尖不小心碰到他的指腹,两人同时缩回手,空气里弥漫着尴尬的沉默。
“谢谢。”她小声说,赶紧用纸巾擦了擦额角的汗,“我今天状态不太好。”
“正常,”男人笑了笑,眼角露出浅浅的细纹,“我昨天为了改论文,在实验室熬到三点,现在看什么都像薛定谔的猫——既对又错。”
这个比喻让林知夏忍不住笑出声。她抬起头,认真打量起眼前的人。他看起来三十岁左右,鼻梁上架着副细框眼镜,镜片后的眼睛里带着点疲惫,却闪着专注的光。桌上的保温杯里泡着菊花茶,旁边放着本翻旧的《高等代数》,书页间夹着张泛黄的便签,上面写着几行潦草的公式。
“你是数学系的?”林知夏问。
“算是吧,”男人点头,“我叫陈砚知,量子信息实验室的,刚回国没多久。”
“林知夏,直博三年级,跟着李教授做微分几何。”她伸出手,又想起自己刚擦过汗,赶紧在衣服上蹭了蹭,“不好意思,手有点湿。”
陈砚知笑着握住她的手,掌心干燥温暖:“没关系,搞数学的手,哪有干净的时候。”
他们的第一次对话,最终停在十一点十五分。陈砚知接了个电话,匆匆收拾东西离开,走之前把那杯没喝完的菊花茶推到她面前:“降温用,我实验室还有。”林知夏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图书馆门口,端起杯子喝了一口,清甜的菊花香混着淡淡的薄荷味,顺着喉咙滑下去,竟真的驱散了几分燥热。
第二天早上,林知夏在老位置发现了一杯新的菊花茶,旁边压着张便签,上面是工整的楷书:“昨天的积分题,我重新推算了一遍,附在后面。陈砚知。”便签背面是详细的解题步骤,每一步都标注着使用的定理,最后还画了个小小的笑脸。
林知夏把便签夹进习题集里,指尖反复摩挲着那个笑脸,嘴角忍不住上扬。她拿出手机,翻出实验室群里的成员名单,找到“陈砚知”的名字,点进他的个人主页。头像是一张星空照片,备注里写着“量子信息与数学物理交叉研究”,个性签名是“数学的尽头是哲学,哲学的尽头是美学”——和她的想法不谋而合。
接下来的一周,林知夏和陈砚知每天都会在图书馆相遇。他们很少长时间交谈,大多时候只是互相递杯热茶,或者在对方的草稿纸上写下解题思路。林知夏发现,陈砚知不仅数学功底扎实,还懂古典音乐,偶尔会在休息时给她讲巴赫的赋格曲如何像数学公式一样严谨;而陈砚知也知道了,林知夏喜欢读加缪的小说,还会弹钢琴,曾经用数学模型分析过《卡门》里的旋律结构。
周五下午,图书馆闭馆整修,林知夏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时,陈砚知叫住了她。
“要不要去实验室看看?”他手里拿着一串钥匙,晃了晃,“我们刚引进了台量子模拟计算机,或许你会感兴趣。”
林知夏犹豫了一下。她和陈砚知虽然每天见面,但严格来说还算陌生人,直接去对方的实验室似乎有些唐突。可看着陈砚知期待的眼神,她还是点了点头:“好啊。”
量子信息实验室在物理楼的顶层,走廊里挂着历代物理学家的照片。陈砚知打开实验室的门,迎面而来的是一阵凉爽的风——这里的空调比图书馆的好用多了。实验室里摆放着各种精密的仪器,中央的操作台上放着台银色的机器,屏幕上显示着复杂的波形图。
“这就是量子模拟计算机,”陈砚知走到机器旁,调出一组数据,“我们用它来模拟量子纠缠态,其实和你们研究的微分几何有共通之处,都是在高维空间里寻找规律。”
林知夏凑过去,看着屏幕上不断变化的曲线,忽然指着其中一段说:“这里的曲率变化,和我最近研究的黎曼流形很像。”
陈砚知眼睛一亮,赶紧调出更详细的数据:“你看这里,如果把量子比特的状态看作流形上的点,那么量子纠缠就是流形之间的映射。”
他们就着屏幕上的数据讨论起来,从量子纠缠到黎曼几何,再到非欧空间的拓扑结构,不知不觉就到了傍晚。窗外的夕阳透过百叶窗,在地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,实验室里只剩下键盘敲击声和偶尔的讨论声。
“原来如此,”林知夏恍然大悟,“我之前一直卡在高维流形的嵌入问题上,现在看来,可以用量子纠缠的模型来解决。”
“我也是,”陈砚知笑着说,“你刚才提到的曲率计算方法,正好能解决我们量子模拟中的误差问题。”
两人相视一笑,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找到知音的喜悦。林知夏低头看了看表,已经七点多了,肚子不合时宜地叫了起来。
“抱歉,”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,“耽误你这么久。”
“没事,”陈砚知关掉电脑,“我也收获很大。一起去吃饭吧?楼下的食堂应该还有饭。”
食堂里人不多,他们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。陈砚知去打饭时,林知夏拿出手机,翻出和导师李教授的聊天记录。李教授昨天还在跟她说,微分几何和量子信息的交叉研究是个新方向,让她多和物理学院的人交流,没想到今天就遇到了陈砚知。
“在想什么?”陈砚知端着两盘饭菜回来,放在她面前,“宫保鸡丁和番茄炒蛋,不知道合不合你口味。”
“谢谢,我很喜欢。”林知夏拿起筷子,夹了块鸡丁放进嘴里,忽然想起什么,“对了,你之前说刚回国,是从哪里回来的?”
“普林斯顿,”陈砚知喝了口汤,“跟着威滕教授做了五年博士后,上个月才回来。”
林知夏惊讶地抬起头。爱德华·威滕是国际著名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, Fields奖得主,能跟着他做研究,足以说明陈砚知的学术水平。
“难怪你对量子数学这么了解,”她由衷地说,“威滕教授的论文我读过几篇,太深奥了。”
“其实也没有,”陈砚知谦虚地说,“威滕教授常说,再复杂的理论,本质上都是简单的逻辑推演。就像你研究的微分几何,看似抽象,其实都是为了描述现实世界的空间结构。”
他们边吃边聊,从学术聊到生活。林知夏知道了陈砚知的老家在苏州,父母都是大学教授,他从小在图书馆长大,五岁就能背出圆周率小数点后一百位;陈砚知也知道了,林知夏的父亲是建筑设计师,母亲是钢琴老师,她小时候学钢琴时,总喜欢把乐谱翻译成数学公式来记,后来干脆转去学了数学。
“这么说,我们都是‘学术家庭’出身?”陈砚知笑着说,“我爸妈总说我太死板,做什么都像解数学题,连找对象都要列个评分表。”
林知夏忍不住笑了:“我妈也总说我,跟人聊天三句话不离公式,以后肯定嫁不出去。”
食堂的灯光柔和地洒在两人身上,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下来,远处传来学生社团的歌声。林知夏看着陈砚知认真倾听的侧脸,忽然觉得,和他在一起的时光,就像解一道完美的数学题——每一步都充满惊喜,每一个推论都恰到好处。
吃完饭,陈砚知送林知夏回宿舍。路上,两人并肩走在未名湖畔,月光洒在湖面上,泛起粼粼波光。
“下周有个学术研讨会,”陈砚知忽然开口,“主题是数学与量子物理的交叉研究,我有个报告,要不要来听?”
“好啊,”林知夏立刻答应,“我正好可以学习一下。”
“不是学习,”陈砚知停下脚步,转过身看着她,眼睛在月光下格外明亮,“是交流。我希望能听到你的想法,知夏。”
林知夏的心跳猛地加速,她看着陈砚知认真的眼神,忽然想起第一次在图书馆见面时,他电脑屏幕上的黎曼猜想公式。她一直觉得,爱情就像一道复杂的数学题,需要严谨的论证和推导,可在这一刻,她忽然明白,有些答案,不需要刻意计算,只需要跟着心走就好。
“我会去的,”她轻声说,声音里带着自己都没察觉的温柔,“一定会去。”
陈砚知笑了,伸手轻轻拂去她头发上的落叶:“那我等你。”
月光下,未名湖的水波轻轻荡漾,远处的博雅塔静静矗立。林知夏看着陈砚知的笑脸,忽然想起习题集扉页上的那句话——“连续不代表可导,如同相爱不代表合适”。她拿出手机,在备忘录里写下新的句子:“但当两个灵魂在高维空间里共振时,所有的论证都成了多余。”
她抬起头,正好对上陈砚知的目光,两人相视一笑,默契地继续往前走。晚风拂过湖面,带着淡淡的荷花香,仿佛在为这道刚刚开始的爱情命题,写下最温柔的注脚。
同类推荐
 别争了,你们兄弟俩都是替身(江颐鹤江衍衡)在线阅读免费小说_完整版小说免费阅读别争了,你们兄弟俩都是替身(江颐鹤江衍衡)
别争了,你们兄弟俩都是替身(江颐鹤江衍衡)在线阅读免费小说_完整版小说免费阅读别争了,你们兄弟俩都是替身(江颐鹤江衍衡)
啾猪猪
 杜若元朗古代医闹?我靠医德服人最新章节阅读_杜若元朗最新章节在线阅读
杜若元朗古代医闹?我靠医德服人最新章节阅读_杜若元朗最新章节在线阅读
四就是四
 古代医闹?我靠医德服人(杜若元朗)热门的小说_热门网络小说推荐古代医闹?我靠医德服人(杜若元朗)
古代医闹?我靠医德服人(杜若元朗)热门的小说_热门网络小说推荐古代医闹?我靠医德服人(杜若元朗)
四就是四
 《断桥上的微光》(苏慧林伟)免费小说全集_完本小说免费阅读《断桥上的微光》(苏慧林伟)
《断桥上的微光》(苏慧林伟)免费小说全集_完本小说免费阅读《断桥上的微光》(苏慧林伟)
祝君好运1319
 古代医闹?我靠医德服人(杜若元朗)热门网络小说_最新章节列表古代医闹?我靠医德服人(杜若元朗)
古代医闹?我靠医德服人(杜若元朗)热门网络小说_最新章节列表古代医闹?我靠医德服人(杜若元朗)
四就是四
 裴泽谢竞(凤冠换命摄政王妃不为刀)免费阅读无弹窗_凤冠换命摄政王妃不为刀裴泽谢竞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
裴泽谢竞(凤冠换命摄政王妃不为刀)免费阅读无弹窗_凤冠换命摄政王妃不为刀裴泽谢竞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
某长生
 纸人镇民国洋场沈雁沈雁免费完结版小说_小说完结纸人镇民国洋场沈雁沈雁
纸人镇民国洋场沈雁沈雁免费完结版小说_小说完结纸人镇民国洋场沈雁沈雁
月下听风鱼
 纸人镇民国洋场沈雁沈雁小说完结推荐_热门小说阅读纸人镇民国洋场沈雁沈雁
纸人镇民国洋场沈雁沈雁小说完结推荐_热门小说阅读纸人镇民国洋场沈雁沈雁
月下听风鱼
 我的病娇女友是精神病院护士(轻轻沈灼)最新好看小说_无弹窗全文免费阅读我的病娇女友是精神病院护士轻轻沈灼
我的病娇女友是精神病院护士(轻轻沈灼)最新好看小说_无弹窗全文免费阅读我的病娇女友是精神病院护士轻轻沈灼
桃子快到怀里来
 沈雁沈雁(纸人镇民国洋场)最新章节免费在线阅读_纸人镇民国洋场最新章节免费阅读
沈雁沈雁(纸人镇民国洋场)最新章节免费在线阅读_纸人镇民国洋场最新章节免费阅读
月下听风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