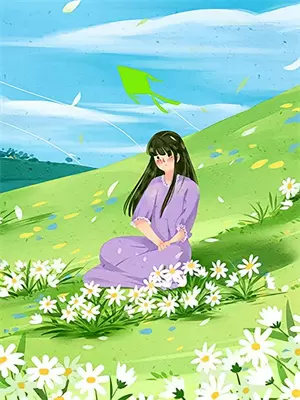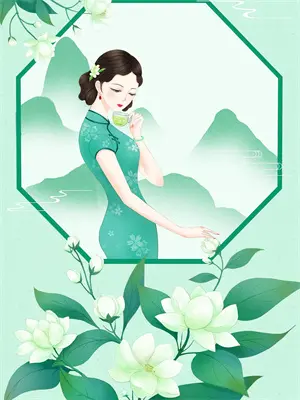
- 锁眼张晓晓林小满小说完结推荐_完整版小说免费阅读锁眼(张晓晓林小满)
- 分类: 悬疑惊悚
- 作者:老爷赏口饭
- 更新:2025-10-11 23:52:04
《锁眼张晓晓林小满小说完结推荐_完整版小说免费阅读锁眼(张晓晓林小满)》精彩片段
第一章:锈迹里的惨叫办公室的中央空调又开始滴水,冰凉的水珠砸在文件柜顶,
嗒、嗒、嗒,像老式座钟的秒针在数着时间。我盯着物证袋里那截卡在旧锁里的扫把枝,
指腹反复摩挲着透明塑料表面。隔着一层薄塑,仍能摸到锁孔边缘凹凸的锈迹,
那锈色不是均匀的暗红,而是像干涸的血痂,一块深一块浅地嵌在黄铜锁身的纹路里。
十七年前的惨叫声就是这时炸开的。不是尖锐的哭喊,是带着气音的闷痛,
像被捂住嘴的猫在喉咙里呜咽。我眼前瞬间浮出那片青砖地,是我们小学教学楼后墙的砖,
被雨水泡得发乌,林小满就蹲在那砖上,校服裙摆沾了泥点,右手死死捂着左眼,
指缝里渗出的血珠砸下来,在砖缝里晕开,像一朵朵没开全就蔫掉的暗红色小花。
那时她的睫毛上还挂着雨珠,混着血水流进衣领,我记得她校服领口的白色棉布,
被染红了一小片,像被墨汁洇开的宣纸。“苏小姐?”对面的王警官轻轻敲了敲桌子,
他无名指上的婚戒蹭过桌面,留下一道细微的划痕。我这才猛地回神,
指腹下的塑料袋已经被攥出了几道白印。低头看掌心,指甲深深掐进肉里,
留下五个弯月形的红痕,渗着一丝细小的血点——和当年林小满指缝里的血,颜色一模一样。
那时我八岁,攥着半截扫把枝站在她面前,枝桠上还沾着刚扫起的粉笔灰,而她的血,
就顺着那粗糙的竹纹往下淌。“这把锁和扫把枝,都是在林小满的出租屋飘窗柜里找到的。
”王警官推过来一份案卷,文件夹边缘磨得有些毛糙,
封面的“失踪案”三个字用红笔标了重点,红色墨水在纸页上晕染,像干涸的血迹。
“她失踪前三天,向公司提交了休假申请,系统里的理由写的是‘处理私人旧怨’,
没有具体说明。”他翻开案卷时,我注意到他袖口露出半截褪色的红绳,
和我奶奶以前戴的那种很像。他抽出一张打印的监控截图推到我面前。
照片里的画面有些模糊,是报社楼下的十字路口,一个穿米色风衣的女人站在公交站牌旁,
宽檐帽压得很低,遮住了大半张脸,只能看见下颌线的弧度,还有风衣下摆被风掀起的一角。
风衣口袋露出半截丝巾,颜色像极了林小满最喜欢的樱粉色。
“这是她最后一次出现在监控里,时间是上周三下午四点十分,就在你工作的报社楼下。
”王警官的声音很平稳,却像锤子敲在我心上,“监控拍到她在站牌旁站了二十分钟,
期间一直在看报社的大门,看起来像是在等什么人。”我猛地抬头,
心脏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紧,连呼吸都滞了半秒。办公室的空调风扫过脖颈,
带来一阵刺骨的凉,后颈的碎发被吹得贴在皮肤上。“不是我,”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颤,
像生了锈的铁片在摩擦,“我根本没见过她,那天下午我一直在排版室改稿子,
同事都能作证。”话虽如此,指尖却控制不住地发抖,连捏着文件的力气都在流失。
传的风言风语此刻在耳边嗡嗡作响——先是有人在茶水间说“苏晓的妈妈以前是小学班主任,
好像还出过事”,接着就有人翻出十几年前的旧帖,说“我表姐跟她们一个班,
当年就觉得苏晓仗着妈妈欺负同学,把人眼睛都弄伤了”。现在林小满失踪,
所有线索都隐隐指向我——那把旧锁是当年我们教室后门的锁,
锁身上还留着我用小刀刻的歪扭字母“SS”;那截扫把枝是我当年用来捅锁眼的东西,
枝桠末端还留着咬痕,是我无聊时用牙啃出来的;连林小满最后出现的地方,
都是我每天上班的报社楼下。仿佛十七年前那截不起眼的扫把枝,终于在土里扎根,
长成了缠向我的荆棘,每一根刺都扎在“霸凌者”“凶手”的标签上,渗出腥甜的血。
第二章:闪光灯下的阴影出租车刚拐进小区门口的巷子,我就看见楼下围了一圈人。
不是平时遛弯的老人,是举着相机、扛着摄像机的记者,有人举着话筒,
话筒上的台标在路灯下闪着光。其中一个记者穿着印有“民生热线”字样的蓝色马甲,
袖口沾着疑似咖啡的褐色污渍。我的心一下子沉下去,让司机在巷口停下,
付了钱就想往旁边的小路躲。那小路两旁堆着建筑垃圾,碎玻璃在月光下闪着危险的光。
可已经晚了。有人看见我下车,立刻喊了一声“是苏晓!”,一群人瞬间涌过来,
相机的闪光灯“咔嚓咔嚓”响个不停,晃得我睁不开眼。离我最近的女记者喷着浓烈的香水,
香奈儿五号的味道混着烟草味,让我胃里一阵翻涌。“苏小姐,
请问你和林小满的失踪有关吗?”一个戴眼镜的男记者把话筒递到我面前,
他的眼镜片上有道裂痕,声音尖锐得像指甲刮过玻璃,
“有人说当年你故意用扫把枝戳伤她的眼睛,是不是真的?
”“林小满失踪前为什么会去报社找你?你们是不是因为当年的事起了争执?
”一个扎马尾的女记者举着录音笔,笔尖几乎戳到我下巴,她手腕上的银镯子晃荡着,
发出细碎的响声。“网上说你妈妈当年用班主任的权力压下了事情,还赔了封口费,
这是真的吗?”问题像冰雹一样砸过来,我往后退了一步,却被后面的记者挡住去路。
后背抵着冰冷的墙,墙上有未干的涂鸦,绿色油漆蹭在我的大衣上,像一道丑陋的伤疤。
我突然想起林小满的左眼——当年医生说,她的角膜受损后,再也不能见强光,
一碰到刺眼的光就会流泪,连晴天出门都要戴宽檐帽。这些记者举着的闪光灯,
是不是也会让她的眼睛疼?她这个念头刚冒出来,就被更浓的恐惧淹没。
我伸出手想推开面前的话筒,却不小心碰到了一个摄像机,镜头晃了一下,
记者立刻叫起来:“你想干什么?心虚了吗?”他的声音在巷子里回荡,
惊飞了墙头上的野猫。“让开,”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,却还是强撑着说,
“我没什么好说的,警察会调查清楚。”可没人让开,反而围得更紧了。
有人伸手想拉我的胳膊,指尖触到我皮肤的瞬间,我猛地躲开,转身往单元楼跑。
高跟鞋踩在石板路上,发出慌乱的“噔噔”声,身后的闪光灯还在亮,
记者的追问声跟着我跑了一路。有个记者喊着“苏晓,看这边!”,
声音里带着不怀好意的兴奋。冲进单元楼时,我几乎是撞开了防盗门,反手锁上门的瞬间,
后背已经被冷汗浸湿,贴在衬衫上,冰凉刺骨。楼道里的声控灯亮了,昏黄的光打在墙上,
映出我狼狈的影子——头发乱了,围巾掉了一半,脸上还沾着不知是谁蹭到的灰尘,
右脸颊被话筒边缘硌出一道红印。我靠着门滑坐在地上,大口喘着气,心脏还在狂跳,
仿佛要撞破肋骨跳出来。手机在口袋里震动,是妈妈打来的。屏幕上显示着“妈”的名字,
旁边是她几年前在公园拍的照片,她穿着红色毛衣,笑得很灿烂。我犹豫了一下,
还是按下了接听键。“晓晓,你没事吧?”妈妈的声音很着急,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,
背景音里有电视新闻的声音,主播正在播报“知名编辑卷入失踪案”的新闻。“我看新闻了,
说记者去你家楼下堵你,你没受伤吧?”“妈,我没事,”我吸了吸鼻子,
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静些,楼道里的声控灯灭了,四周陷入黑暗,只有手机屏幕亮着,
映出我通红的眼睛。“就是有点累。”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,久到我以为信号断了,
然后传来妈妈小心翼翼的声音:“晓晓,当年的事……你真的是不小心的,对不对?
”这句话像一根针,扎破了我强装的镇定。我靠在冰冷的门上,眼泪突然就掉了下来,
黑暗中,泪水划过脸颊,留下冰凉的痕迹。“妈,我是不小心的,我真的不是故意的,
”我哽咽着,声音断断续续,“可现在所有人都觉得我是凶手,
都觉得你当年压下了事情……他们说我是霸凌者,说你是……是滥用职权……”“别担心,
”妈妈的声音也带了哭腔,却还是在安慰我,我听见她那边传来茶杯放在桌上的声音。
“妈会想办法,当年能解决,现在也能。 你先好好休息,别想太多,妈明天就去市里找你。
”挂了电话,我坐在地上哭了很久。楼道里的声控灯灭了,一片漆黑,只有手机屏幕亮着,
映出我通红的眼睛。我想起当年妈妈也是这样,在我戳伤林小满的眼睛后,她把我拉到身后,
对着林小满的父母鞠躬道歉,说“都是我没教好女儿”,然后拿出一笔钱,说“这是医药费,
不够再跟我说”。那时她的腰弯得很低,像一株被风雨压弯的稻穗。我不知道自己坐了多久,
直到楼道里传来邻居开门的声音,声控灯再次亮起,我才慌忙站起来,抹掉眼泪,
快步往楼上走。打开家门的瞬间,一股冷清的气息扑面而来。房子是去年买的,两室一厅,
装修得很温馨,沙发上还放着我没叠好的毯子,茶几上有喝了一半的咖啡杯,
可现在却觉得空荡荡的,连灯光都显得冰冷。墙上的时钟指向十一点,秒针滴答作响,
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。第三章:深夜的脚步声夜里,我总听见门外有脚步声。
起初以为是邻居起夜,或者是楼下的人上楼,可仔细听,那脚步声就在我家门口的楼道里,
不高不低,轻缓得像女生穿平底鞋走路的声音,一步、两步、三步,在门口停几秒,
然后又慢慢走开。有时能听见鞋跟蹭过地面的细微声响,像是穿着帆布鞋的人在徘徊。
我猛地睁开眼,卧室里一片漆黑,只有窗帘缝里透进一丝微弱的月光,照亮了衣柜的轮廓。
床头柜上的闹钟显示凌晨两点半,秒针滴答滴答地响,和门外的脚步声混在一起,
听得人心里发毛。我屏住呼吸,悄悄掀开被子,赤脚踩在地板上,
冰凉的触感让我打了个寒颤。我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口,透过猫眼往外看。
楼道里的声控灯没亮,一片漆黑,什么都看不见。只有走廊尽头的窗户透进一点光,
照亮了楼梯口的轮廓。可刚转身,就听见脚步声又响了起来,这次比刚才更近,
像是有人站在门口,贴着门在听里面的动静。我甚至能想象出那人侧耳倾听的样子,
也许正透过猫眼看着里面,眼神冰冷。我的后背一下子就凉了,靠在门后,大气都不敢出。
手心全是汗,紧紧攥着门把手,指节发白。过了几分钟,脚步声慢慢走远,
消失在楼梯口的方向。我却不敢回床上,就那样靠在门后,直到天边泛起鱼肚白,
第一缕阳光透过窗帘缝隙照进来,才敢稍微放松一点。接下来的几天,
每天夜里都会有脚步声。有时是轻缓的,像在门口徘徊;有时是急促的,
仿佛有人在楼道里追赶什么,脚步声“噔噔噔”地响,伴随着模糊的喘息声。有一次,
我甚至听见了女人的抽泣声,断断续续,像是压抑了很久的委屈。我每次透过猫眼往外看,
都只有声控灯亮着的空荡荡的走廊,连个人影都没有。走廊的墙皮有些剥落,
露出底下的水泥,在灯光下显得格外荒凉。可一转身,又觉得客厅里有人。有一次,
我从卧室出来想喝水,眼角的余光瞥见沙发上坐着一个人,穿着米色风衣,戴着宽檐帽,
侧脸的轮廓在昏暗的灯光下像极了林小满。她的肩膀微微耸动,像是在哭泣。
我吓得手里的水杯“哐当”一声掉在地上,水洒了一地,再看沙发时,那里空荡荡的,
只有一个抱枕掉在地上。地板上的水渍在灯光下闪着光,像眼泪。是幻觉,一定是幻觉。
我蹲在地上捡玻璃碎片,手指被划破了,血珠滴在地板上,
和当年林小满滴在青砖上的血一样红。我突然就蹲在地上哭了,不知道是因为手指疼,
还是因为心里的恐惧。黑暗中,我仿佛又听见了那声闷痛的惨叫,在耳边回荡。我开始失眠,
每天晚上都睁着眼睛到天亮,眼皮沉重得像灌了铅,可脑子却异常清醒,全是林小满的影子,
还有门外的脚步声。白天上班时,我坐在电脑前,盯着屏幕上的文字,却一个字都看不进去,
眼前总晃着闪光灯的光,耳边总响着记者的追问声。有一次,我在茶水间倒水,手一抖,
热水洒在手上,烫出一片红印,可我却浑然不觉,直到同事惊呼着帮我冲凉水,我才回过神。
同事们看我的眼神也变了。以前在茶水间碰到,大家会笑着打招呼,
聊几句家常;现在看到我,要么低下头假装没看见,要么匆匆走开。
偶尔还能听见有人在背后小声议论,“就是她,当年把同学眼睛弄伤了,现在同学失踪了,
说不定真跟她有关”。有个平时关系不错的同事,有次在电梯里碰到我,
下意识地往旁边挪了挪,像是怕被我传染什么似的。那一瞬间,我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,
疼得说不出话。我受不了这样的眼光,也受不了心里的恐惧,只能去药店买了安眠药。
晚上睡前吃一片,就能勉强睡上几个小时。
可梦里全是锁孔里那双含泪的眼睛——林小满的左眼,隔着锁孔看着我,
眼里满是委屈和痛苦,还有她捂着眼睛哭着说“我看不见了”的样子,
声音一遍又一遍地在我耳边回响。梦里的场景总是在那片青砖地,下着雨,她的血混着雨水,
在地上汇成一条小溪,而我站在溪水里,怎么也走不出去。有天早上,我被手机铃声吵醒,
是报社领导打来的。他让我去趟办公室,语气很严肃。我心里咯噔一下,知道肯定没好事。
来到报社,走进领导办公室,他坐在办公桌后,手里拿着一份文件,脸色凝重。
办公桌上放着一盆绿萝,叶子有些发黄,像是很久没人浇水了。“苏晓,”他开口,
声音低沉,“最近关于你的舆论影响很不好,很多读者给报社打电话,
说不想再看到你的稿子,还有几个合作方也提出要暂停合作。”他推了推眼镜,镜片反光,
看不清他的眼神。我低着头,手指紧紧攥着衣角,等着他接下来的话。“报社研究决定,
让你先停职待查,”领导叹了口气,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,放在桌上,“等警察调查清楚,
舆论平息了,你再回来上班。这期间,你的工作会由其他同事接手,
你把手头的事情交接一下吧。”信封是牛皮纸的,边角有些磨损。停职待查。
这四个字像一块石头,砸在我心上,让我瞬间喘不过气。我张了张嘴,想替自己辩解,
想说“我没做错什么”,可话到嘴边,却变成了一句无力的“好”。走出领导办公室,
同事们都在看着我,眼神里有同情,有好奇,还有些幸灾乐祸。我快步穿过办公室,
回到自己的工位,收拾东西。桌上还放着我昨天没改完的稿子,
标题是“城市里的温暖瞬间”,可现在看来,多么讽刺。抽屉里有我和大学同学的合影,
照片上的我们笑得很灿烂,可现在,那些笑容在我眼里都变得模糊了。收拾好东西,
我抱着纸箱走出报社。这次楼下没有记者,阳光很好,照在身上却没有一点暖意。
我沿着马路慢慢走,不知道该去哪里,也不知道该做什么。手机在口袋里震动,
是妈妈发来的微信:“晓晓,妈到市里了,在你家楼下,你在哪?”我看着手机屏幕,
突然就觉得很委屈,眼泪又掉了下来。原来在我最无助的时候,只有妈妈会一直陪着我。
路上的行人匆匆走过,没人注意到一个抱着纸箱的女人在路边哭泣。
第四章:旧照片里的舆论风暴回到家时,妈妈已经在楼下等了很久。她穿着一件灰色的外套,
头发有些乱,手里拎着一个大包,里面装着给我带的吃的——有我小时候最爱吃的辣白菜,
还有她自己做的豆包。看见我回来,她立刻迎上来,接过我手里的纸箱,纸箱很重,
她的胳膊晃了一下,差点没拿稳。“怎么拿这么多东西?是不是出什么事了?
”她的声音带着担忧,眼角的皱纹更深了。我没说话,跟着她上楼。打开家门,
妈妈把东西放在玄关,转身看着我,她的眼睛有些红肿,像是哭过。
“是不是报社那边有什么说法?”我点了点头,坐在沙发上,把停职的事告诉了她。
妈妈听完,坐在我身边,轻轻拍着我的背,她的手心很暖,带着常年做家务留下的薄茧。
“没事,停职就停职,正好休息几天,等警察调查清楚,他们自然会让你回去上班。
”“可网上的人都在骂我,”我靠在妈妈肩上,眼泪又掉了下来,客厅的灯光很亮,
照得我眼睛发酸。“他们说我是霸凌者,说你当年用权力压下了事情,
还说那笔钱是封口费……妈,我真的好难受。”窗外传来汽车驶过的声音,很遥远。
妈妈沉默了很久,久到我以为她不会说话了,然后她拿起手机,点开一个网页递给我,
“你看,这是当年林小满家给我写的感谢信,还有医院的缴费单,我一直都存着,
就是怕有一天说不清楚。”手机屏幕上是一张扫描的信纸,字迹有些潦草,
却是林小满妈妈的笔迹——当年我见过她写的字,很清秀。信上写着:“感谢刘老师的帮助,
小满的手术很成功,医生说视力能恢复到0.8,以后再也不用怕看不见了。
这笔钱我们会记着,等小满长大了,一定还您。”下面还有一张医院的缴费单,
日期是当年的9月15日,金额是208600元,收款项目是“左眼角膜修复手术费”,
缴费人是妈妈的名字。缴费单的边缘有些泛黄,像是被人反复看过。
“当年小满的左眼不是你戳伤的,”妈妈的声音有些哽咽,她拿起茶几上的水杯,喝了一口,
水已经凉了。“她天生左眼弱视,医生说如果不及时手术,很快就会彻底失明。
她家里条件不好,拿不出手术费,我知道后,就以你的名义给了他们一笔钱,
让他们带小满去做手术。”我愣住了,看着手机屏幕上的感谢信和缴费单,眼泪流得更凶了,
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棉花,说不出话。“妈,你为什么不告诉我?
为什么让我以为是我戳伤了她的眼睛?”我看着妈妈,心里又委屈又生气,这么多年的愧疚,
原来都是一场误会。“我怕你知道后不珍惜,”妈妈叹了口气,眼神里充满了疲惫,
她鬓角的白发在灯光下格外显眼。“那时候你才八岁,特别调皮,总爱欺负同学。
我想让你记住这个‘教训’,让你知道伤害别人是要付出代价的,以后才能懂事,
才能学会尊重别人。我跟小满的父母商量好了,让他们配合我,说小满的眼睛是你戳伤的,
让她转学,这样你就不会知道真相。”“可你知不知道,这十几年我一直活在愧疚里?
”我看着妈妈,声音里带着哭腔,“我每天都在想,是我把林小满的眼睛弄伤了,
是我毁了她的人生。现在她失踪了,所有人都觉得是我干的,我真的快撑不下去了。
”我想起那些失眠的夜晚,想起梦里反复出现的场景,心里一阵阵地抽痛。妈妈抱着我,
哭着说:“是妈错了,妈不该瞒着你,不该让你受这么多委屈。你放心,
这次妈一定会把真相说出来,不会再让你受冤枉。”她的眼泪滴在我的头发上,冰凉的。
可妈妈还没来得及说真相,网上的舆论就彻底失控了。有人扒出了我小学时的班级合影,
照片上的我们穿着蓝色的校服,站在教学楼前的花坛旁。花坛里种着月季,开得正艳。
发帖的人用红色的圈把我和林小满圈了出来,
配文“霸凌者与受害者的早期合影——前排左三是苏晓,后排右二是林小满,
当年苏晓就是这样站在林小满面前,用扫把枝戳伤了她的眼睛”。照片下面有很多评论,
有人说“一看苏晓就不是好东西,眼神里透着一股子嚣张”,有人附和“小时候就这么凶,
长大了做出什么事都不奇怪”,还有人开始扒我的个人信息,
包括我现在住的小区、以前的学校,甚至我妈妈退休前的工作单位。
有个账号贴出了我大学时的照片,配文“看看这跋扈的样子,霸凌惯犯无疑了”。
更过分的是,一个自称“小学同班同学”的账号发了长帖,说“我当年就坐在她们后排,
亲眼看见苏晓把扫把枝塞进锁眼,还故意把林小满推倒在青砖地上,林小满哭着说眼睛疼,
苏晓还笑着说‘谁让你跟我抢座位’”。帖子里还添油加醋地描述了“苏晓妈妈来学校后,
把林小满家长拉到办公室关了半小时,出来后林小满妈妈就哭着说不追究了”,
最后总结“这就是有权有势的人欺负普通人,十几年了,终于要真相大白了”。
这条帖子在网上疯传,不到半天就上了热搜,
#苏晓霸凌同学# #苏晓妈妈滥用职权# 两个话题牢牢占据热搜榜前十。
我手机里的短信和微信被轰炸,陌生号码发来的辱骂信息一条接一条,
“凶手”“滚出这个城市”“你怎么不去死”,不堪入目的字眼像针一样扎进眼里。
有个号码连续发了十几条信息,内容都一样:“你会遭报应的。”妈妈拿着手机,
手指气得发抖,“这些人怎么能这么造谣?当年明明不是这样的!”她想在网上发帖澄清,
可刚编辑好文字,就被无数条辱骂评论淹没,有人说“现在出来洗白晚了”,
有人说“拿不出证据就别装可怜”,还有人威胁“再洗白就去你家楼下堵你”。
妈妈的账号很快就被举报禁言了,她看着手机屏幕,眼泪无声地掉了下来。
我看着妈妈通红的眼睛,心里又疼又悔。如果当年我没有那么调皮,
如果妈妈没有选择隐瞒真相,是不是现在就不会变成这样?我抢过妈妈的手机,关掉网页,
“妈,别发了,没用的,现在他们根本不会听我们的。”我知道,在汹涌的舆论面前,
我们的声音太微弱了。那天下午,我和妈妈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,谁都没说话。
窗外的阳光渐渐暗下来,乌云遮住了天空,像要下雨的样子。妈妈突然站起来,走进卧室,
拿出一个旧箱子,里面全是我小时候的东西——玩具、奖状、还有一本厚厚的相册。
箱子是木头的,上面刻着我的名字,是爸爸以前给我做的。她翻开相册,指着一张照片,
“你看,这是你和小满第一次一起捡槐花的照片,那天你们玩得可开心了,
小满还把她的糖分给你吃。”照片上的我和林小满蹲在老槐树下,
手里捧着满满一捧白色的槐花,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。那时的阳光很暖,照在我们身上,
槐花香飘得很远。我看着照片,眼泪又掉了下来。原来小时候的我们,也曾那么要好。
可为什么后来会变成这样?为什么一件被隐瞒的善意,会变成十几年后的噩梦?就在这时,
我的手机突然响了,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,只有一句话:“想知道林小满在哪,
明天下午三点,老地方见。”“老地方”——这三个字像一道闪电,劈开了我混乱的思绪。
我知道,她说的是我们小学时的后操场,那里有一棵老槐树,
当年我和林小满还一起在树下捡过槐花,一起在树旁的石凳上写作业,
一起在树底下分享偷偷藏起来的零食。那时的石凳上还有我们用粉笔写的歪歪扭扭的字,
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。是谁会知道“老地方”?是林小满吗?还是……和她失踪有关的人?
我握着手机,手指因为紧张而发白。妈妈凑过来,看见短信内容,脸色瞬间变了,“晓晓,
同类推荐
 苏晚厉寒(女友的男闺蜜,是她的灵魂伴侣。)全本免费在线阅读_苏晚厉寒全集在线阅读
苏晚厉寒(女友的男闺蜜,是她的灵魂伴侣。)全本免费在线阅读_苏晚厉寒全集在线阅读
游天地寻龙鳞
 我靠当太子妃升职加薪林烬唐笑笑最新小说推荐_完结小说我靠当太子妃升职加薪(林烬唐笑笑)
我靠当太子妃升职加薪林烬唐笑笑最新小说推荐_完结小说我靠当太子妃升职加薪(林烬唐笑笑)
亚里士多糖
 《这个世界只有我能看到血条》林辰林辰已完结小说_这个世界只有我能看到血条(林辰林辰)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
《这个世界只有我能看到血条》林辰林辰已完结小说_这个世界只有我能看到血条(林辰林辰)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
每日更新持续关注
 青铜门后的修复师张起灵沈知微最新章节在线阅读_张起灵沈知微全本免费在线阅读
青铜门后的修复师张起灵沈知微最新章节在线阅读_张起灵沈知微全本免费在线阅读
睡前故事自我编撰师
 夏知意陆星河星光尽头等你最新章节在线阅读_夏知意陆星河完整版阅读
夏知意陆星河星光尽头等你最新章节在线阅读_夏知意陆星河完整版阅读
景瑞
 夺子封后?我转身辅佐新王炸翻你江山柳若云裴昭完本完结小说_完本完结小说夺子封后?我转身辅佐新王炸翻你江山(柳若云裴昭)
夺子封后?我转身辅佐新王炸翻你江山柳若云裴昭完本完结小说_完本完结小说夺子封后?我转身辅佐新王炸翻你江山(柳若云裴昭)
文文九九
 青囊风水录(苏清瑶林砚)推荐小说_青囊风水录(苏清瑶林砚)全文免费阅读大结局
青囊风水录(苏清瑶林砚)推荐小说_青囊风水录(苏清瑶林砚)全文免费阅读大结局
慕霞玲玲
 净尘戎寒废土拍卖买下全人类最强战力最新章节在线阅读_净尘戎寒完整版阅读
净尘戎寒废土拍卖买下全人类最强战力最新章节在线阅读_净尘戎寒完整版阅读
蒜头天尊
 别后玫瑰自成诗蒋危蒋修宴最新小说推荐_完结小说别后玫瑰自成诗(蒋危蒋修宴)
别后玫瑰自成诗蒋危蒋修宴最新小说推荐_完结小说别后玫瑰自成诗(蒋危蒋修宴)
给口饭吃吧
 体育课李莉(被家长实名举报不占课我取消了体育课)最新章节免费在线阅读_被家长实名举报不占课我取消了体育课最新章节免费阅读
体育课李莉(被家长实名举报不占课我取消了体育课)最新章节免费在线阅读_被家长实名举报不占课我取消了体育课最新章节免费阅读
菩提小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