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- 为我酹酒覆春衫破庙阿黄小说免费完结_最新章节列表为我酹酒覆春衫(破庙阿黄)
- 分类: 言情小说
- 作者:闽中老林
- 更新:2025-09-23 19:01:02
《为我酹酒覆春衫破庙阿黄小说免费完结_最新章节列表为我酹酒覆春衫(破庙阿黄)》精彩片段
离山那日,师父说江湖最爱折断少年人的脊骨。
我们嗤之以鼻,五人沽酒登舟,笑骂天地皆在杯中。
后来惊才绝艳的二师兄为护流民,甘受朝廷招安,却因不肯同流合污被诬陷谋反,万箭穿身时仰天惨笑:“原来脊骨真的这么容易断!”
温柔腼腆的小师弟为救被困的义军领袖,孤身潜入敌营,事成后却被疑与官府有染,受尽酷刑而不辩,自毁容颜沉于寒江。
最是跳脱爱笑的三师妹,为揭露一桩惊天阴谋,假意委身高官,身份败露后于闹市口服毒,死前散尽钗环任由践踏,只求“莫污我清白身”。
大师兄目睹一切后一夜疯癫,逢人便问:“你见我的剑了吗?它怎就钝得斩不断这污糟世道?”
最后只剩我,双鬓斑白,撑着一叶孤舟重走当年路。
江水尽头,忽见昔日五人身影倒映水中,举杯邀我同饮。 我俯身去捞,指尖触到的,唯有冰凉的月亮。
---
山间的晨雾总是散的很迟,像一匹扯不开的绉纱,湿漉漉地缠在人的鬓角衣襟。
我们离山那日,却是少见的一个爽利晴天。
天光劈开云障,将师门那几重熟悉的飞檐黛瓦照得晃眼,几乎有些陌生的锐利。
师父立在石阶尽头,灰白的须发被风拂动,身影却凝然如山壁。
他目光沉沉,自我们五人意气飞扬的脸上一一掠过,最后,只哑声说了一句:“江湖啊…最爱折断少年人的脊骨。你们…好自为之。”
彼时山风正浩荡,吹得我们袍袖猎猎作响,满腔的热血与抱负几乎要破膛而出,哪听得进这般“丧气”话。
二师兄楚珩朗声一笑,眉眼疏狂,是能劈开阴霾的利剑:“师父且宽心!待弟子们斩尽世间不平事,回来与您老人家痛饮三年!”
小师弟云舒抿着唇,悄悄拉我的袖子,眼底却也是亮晶晶的憧憬。
三师妹柳莺已是拍手雀跃:“走啦走啦!先去沽酒!这天下,合该在我辈杯中!”
大师兄沈默负手而立,唇角噙着惯常的温淡笑意,只道:“莫让船家等久了。”
五人一行,笑声惊起了林间宿鸟。
下得山去,江边早有扁舟系柳。
二师兄将新沽来的酒坛泥封一掌拍开,浓烈的酒气混着水汽扑面而来,他率先跃上舟头,振臂高呼:“天地皆在杯中!吾辈同饮!”
糙制的酒碗撞在一起,溅出的酒液如同我们那时挥霍不尽的豪情。
小舟解缆,乘着风,兑着烈酒,载着五颗恨不能立时捧出给天下看的赤心,驶入了茫茫烟波。
江天浩渺,我们笑骂争论,仿佛锦绣前程、澄明世道,真的就在那桨声欸乃处,触手可及。
许多年后,我才品出那碗酒的滋味,原是浮生一场大醉,醒时只剩剔骨剜心的痛。
最先折的是楚珩。
他那般惊才绝艳,本应是悬于浊世的一轮明澈孤月,却偏偏陷进了最污糟的泥淖里。
北地战乱,流民哀鸿遍野,朝廷兵马坐视不理,反以“剿匪”为名屠戮百姓。
他一人一剑,护着数千老弱妇孺退守荒城,粮尽援绝。
城外是黑压压的敌军,城内是日夜不绝的啼哭。
朝廷抛来了招安的橄枝,条件是他楚珩一人入帐。
他去了。
我们都知他为何而去。
为那一口活命的粮,为那一条条卑微如草芥的人命。
可他忘了,那庙堂之高,早已烂到了根子里,岂容得下他一身嶙峋傲骨?
不过半年,京中便传来惊天消息——将军楚珩,拥兵自重,意图谋反,证据确凿。
他被围在校场之上,万箭所指。
听说他那时竟笑了起来,笑声凄厉惨然,穿透了重重营帐,惊散了满天寒鸦:“原来…原来脊骨真的这么容易断!”
箭矢破空之声如疾雨,顷刻吞没了那不甘的嘶吼。
那一身硬骨,最终碎得无声无息。
云舒去收的尸。
我们甚至不敢想,那个连练剑伤到手都要偷偷藏起来怕人看见的、最是温柔腼腆的小师弟,是怀着怎样的心情,去面对二师兄那具被鲜血浸透、钉满箭簇的尸身。
他自此便沉默了。
而后江南义军领袖遭困,需人潜入虎穴营救。
那龙潭虎穴,便是当日诬陷楚珩、如今正大肆搜捕义士的巡抚衙门。
云舒站起身,只说了三个字:“我去吧。”
他成功了,以难以想象的机敏和代价,将人从死牢里换了出来。
可他撤退时露了行迹,被巡抚的亲兵一路追杀,虽侥幸逃脱,却落下了疑点——那般天罗地网,他一个半大少年,如何能全身而退?
流言骤起,窃窃私语,如毒蛇吐信:莫非…他与官府早有勾结?此次救人,不过苦肉之计?甚至…二师兄之死,是否也……
无人听他辩解。
或许他根本未曾辩解。
他只留下一封字迹模糊的信:“此身清白,天地不知,江河或可知。”
三日后,有人在城外寒江下游,捞起一具面目全非的尸身。
脸孔被石头反复砸烂,又被水泡得肿胀,唯能从衣衫佩玉认出是云舒。
他沉入那冰彻骨髓的江水时,怀里还紧紧揣着楚珩当年送他的一枚小小的玉扣。
柳莺哭了三日,又笑了三日。
然后她擦干眼泪,描眉敷粉,穿上最时兴的绫罗衣裙,将自己送进了那位一手策划了楚珩冤案、又下令追捕云舒的高官府中。
她原本是我们中最跳脱爱笑的一个,像山间最不受管束的黄莺儿。
我们都以为她会闹个天翻地覆,她却只是笑,周旋在那些她恨不能食肉寝皮的仇敌之间。
直到那桩牵连无数、足以震动朝野的漕运贪墨与边军粮饷阴谋,被她拿到铁证,秘密送出。
她败露得毫无征兆。或许是那高官早已察觉,猫捉老鼠般看着她挣扎。
她被堵在府内,兵刃加身。
闹市口,囚车木笼。她穿着囚衣,发髻散乱,却挺直着背。
监斩官厉数其罪,她恍若未闻,只从容地从袖中取出早已备好的毒药,一饮而尽。
药性发作极快,鲜血从她唇角溢出,她却挣扎着,用力扯下发间那支高官赏她的珠钗,狠狠掷于地上,又奋力褪下腕间玉镯,任其摔得粉碎。
她环视周围黑压压的、或麻木或好奇的看客,用尽最后气力,声音嘶哑却清晰:“散与你们…拿去…莫污我…清白身……”
钗环零落,被无数只脚踩进泥泞。
那双最爱笑着唤师兄的眼睛,渐渐失了光亮。
沈默带着我,挤在人群里,看完了全程。
他死死攥着我的胳膊,指甲深陷进我肉里,我却感觉不到痛,只因他全身都在抖,抖得像是下一刻就要散架。
回去后,他便不见了。我们再找到他时,是在城外荒废的校场旧址——据说,那是楚珩当年被万箭穿身的地方附近。
他衣冠不整,发丝凌乱,眼神空茫地在一片荒草残垣间跌跌撞撞地走,逢人便抓住急问,声音里带着一种孩童般的惶惑与不解:
“你见我的剑了吗?”
“很强的,能斩断一切邪祟的那种。”
“它怎的就…钝了呢?”
他反复地问,痴痴地笑,泪水纵横了满脸:“钝得…斩不断这污糟世道了…斩不断了……”
那晚之后,江湖上再没有那个温润持重、总在我们闹得过分时无奈一笑的大师兄沈默。
只有一个疯癫的、终日寻剑的乞丐。
而今,只剩我了。
江水千年如一日的流,似乎从未见证过那些鲜活的死亡与疯癫。
我撑着一叶孤舟,溯流而上。
两岸青山依稀旧貌,只是人间早已换过。
双鬓是什么时候斑白的?
我不记得了。
似乎是一夜之间,又像是被那数十载的风,一刀一刀,慢慢刮去了所有黑亮的颜色。
舟行缓缓,每处江湾,每道落日,都像是沉重的烙印,烫在早已枯涸的心底。
这里,我们曾泊舟夜饮,酒碗撞碎水中星月;
那里,楚珩曾仗剑而起,惊走一股水匪,回头冲我们扬眉一笑;
更远处,云舒小心地放走一只受伤的水鸟,柳莺笑着唱起一支忘了词的山歌,沈默则静静坐在船头,将我们的笑闹声下酒……
往日种种,历历在目,又隔着一层永远无法穿透的琉璃。
触手可及,触手便碎。
孤舟行至江心,开阔处,水天一色,落日熔金,将满江流水染成一片血色的苍茫。
我怔怔望着那晃动的金波,忽觉眼涩。
水波荡漾间,光影诡谲地扭曲、聚合,竟渐渐凝出五道倒影。
青衫磊落的楚珩正举着酒坛酣饮,眉眼恣意;
云舒在一旁抿唇浅笑,温柔腼腆;
柳莺裙裾飞扬,笑得没心没肺,正指着天边的飞鸟说什么;
沈默负手而立,唇角是令人心安的温淡笑意;
还有一个…是那时眼神尚且清亮、不知愁为何物的我自己。
他们影影绰绰,立在如镜的水面上,仿佛从未经历那些肮脏与破碎,仍是当年离山时的模样。
楚珩回过头,仿佛看见了我,将手中的酒碗遥遥一举,邀我同饮。
刹那间,胸中那座被岁月尘封、被痛苦凝固的冰壳轰然炸裂,一股酸热猛地冲上喉头鼻尖。我几乎是踉跄着扑到船边,不顾一切地伸出手,向那片虚幻的光影抓去——
指尖触到的,唯有冰凉的、碎了的月亮。
我扑在船沿,大半个身子探出舟外,江水浸湿了我的前襟,冰冷刺骨。
那冰凉的月亮碎在我指间,化成粼粼的波光,晃得人眼晕。
水中的倒影被这一搅,彻底散了,只剩下破碎的光斑,和一张映在水里、双鬓斑白、写满惊惶与未干泪痕的脸。
那是谁?
不是楚珩的疏狂,不是云舒的腼腆,不是柳莺的明媚,不是沈默的温淡,更不是…不是当年那个眼里有光、以为酒杯里能装下整个江湖的自己。
指尖滴着水,冷意顺着指尖爬满了胳膊,钻进心里。
舟子在水面上轻轻打着转,四野无声,只有水波拍打船帮的轻响,一遍,又一遍,像是永无止境的叹息。
我慢慢地缩回身子,湿透的衣袖贴在皮肤上,沉甸甸的。
我坐在那里,很久没有动。
天边的血色彻底褪尽,换上一种沉郁的靛蓝,星子稀疏地亮起来,冷冰冰地缀在空中。
江湖。
师父说,江湖最爱折断少年人的脊骨。
我们不信。
楚珩的脊骨,断在了万箭之下。
云舒的脊骨,沉在了寒江底。
柳莺的脊骨,碎在了闹市口的尘埃里。
沈默的脊骨…他没断,他只是不要了,他把它弄丢了,连同他的剑和他的清醒,一起扔给了这个他斩不断的污糟世道。
我呢?
我的脊骨还在,它撑着我活了下来,撑着我双鬓斑白,撑着我回到这里,看这山水依旧,看这江水无言地流。
它没断,它只是弯了,被这些年压下来的东西,一点一点,压成了一道弧。沉默的,隐忍的,一道属于幸存者的、屈辱的弧。
孤舟再度漂起,顺流而下,不再是溯游追寻,只是漫无目的地漂着。
白日追着黑夜,江湾连着险滩。
我经过繁华的码头,听见酒肆里传来划拳行令的喧哗,恍惚间像是回到那年,酒气混着少年人的壮志冲上云霄。
我经过荒废的城镇,断壁残垣间似有冤魂哭泣,又像是云舒沉江前那无声的诘问。
更多的时候,只是寂静山水,无穷无尽。
偶尔会上岸,买些吃食,补充清水。人们看我一个白发老叟,撑着一叶破旧小舟,眼神多是漠然或怜悯。
有时会遇到一两个江湖人,骑着高头大马,佩着刀剑,意气风发地谈论着某某又做了哪件惊天动地的大事,或是哪两家又结了仇,即将火并。
他们的声音年轻而响亮,带着一种熟悉的、未被磋磨过的锐气。
我总是低下头,匆匆走开。
像怕惊扰了什么,也像怕被什么惊扰。
有一夜,泊在一处荒僻的野渡。岸上传来打斗声,金铁交鸣,夹杂着怒吼与惨叫。
我蜷在舟中,一动不动。
很快,声音歇了,只剩下粗重的喘息和翻捡东西的窸窣声。
“老大,还有个船!”
脚步声逼近,火把的光亮跳动着,映出几张带着血污和贪婪的脸。
“老头,滚下来!船和钱留下,饶你一条老命!”
我慢慢站起身,看向他们。
三个彪形大汉,手里提着还在滴血的刀。
江湖。
这就是江湖。
不是诗酒风流,不是快意恩仇,是血污,是掠夺,是最直接的生与死。
其中一人已不耐烦,一步踏上船头,小船猛地一倾。
他伸手就来抓我衣襟。
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,
或许是这数月重走旧路积攒下的所有枯寂与悲怆,在这一刻找到了一个出口。
我没有闪躲,反而迎上前一步,干枯的手快得不像老人,一把攥住了他持刀的手腕。
那汉子一愣,显然没料到这干瘪老叟竟敢反抗,随即狞笑:“老东西找死!”
他发力欲挣脱,却猛地发现那枯爪般的手竟纹丝不动,一股巨力传来,捏得他腕骨咯咯作响。
他惨叫一声,钢刀脱手落下。
我另一只手接住下落的刀,看也没看,反手一划。
动作滞涩,毫无美感可言。
甚至不像一招剑法或刀法。
只是最本能的一挥。
血光迸现。那汉子捂着喉咙,难以置信地瞪着我,嗬嗬作响地倒栽进江里。
剩下的两人惊得倒退一步,火把的光映着我满是皱纹的脸和手中滴血的刀。
我抬起头,看着他们。
我的眼神一定很空,很静,静得像这深夜的江水,底下却翻涌着他们看不懂的、积压了一生的东西。
我没有说话。
那两人对视一眼,竟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惧意。
他们啐了一口,骂骂咧咧,却终究没再上前,拖着同伴的尸体,迅速消失在黑暗中。
火把被扔在地上,渐渐熄灭。
四周重新陷入黑暗和死寂。
只有水声,和浓郁得化不开的血腥味。
我丢开刀,那刀沉入江中,连一丝声响都无。我慢慢坐回船板,看着自己枯瘦的、微微颤抖的手。
原来,还会杀人。
师父教的剑法,还没忘干净。
只是这手,如今更惯于握桨,而非握剑了。
那一夜之后,我似乎连最后那点支撑着“重走”的意念也耗尽了。
孤舟真正成了随波逐流的飘萍。
困了便睡,醒了便看着江水发呆,饿了便吃些干粮,渴了便掬一捧江水。
有时会遇到雨,淅淅沥沥,将天地连成灰蒙蒙的一片。
我便坐在舟中,任雨打湿全身,一动不动,像是化成了江心的一块石头。
恍恍惚惚间,总觉得他们还在。
有时觉得楚珩就坐在船头,回头冲我笑:“小五,酒没了,前头镇子记得去打。”
有时听见柳莺在哼那支忘了词的歌,调子飘忽,听不真切。
有时感觉云舒在轻轻拉我袖子,小声说:“师兄,雨大了,进舱吧。”
有时,又似乎听见沈默在耳边叹息,那叹息沉重得压弯了雨丝。
可我猛地转头,
船舱空空,
只有雨水从篷沿滴落,
嗒,
嗒,
嗒……
像是时光流逝的声音。
这一日,舟行至一处极为宽阔的江面,水势平缓,烟波浩渺,对岸的山影淡得如同墨迹滴入清水。
天色已近黄昏,落日半沉在水天相接处,将云彩和水面烧成一片连绵的、近乎悲壮的赤金。
我记得这里。
当年离山,顺流而下,第一夜泊宿,便是此处。
那晚,我们喝光了所有的酒,对着江心的月亮大声念着幼稚而热切的誓言,说要荡尽天下不平,要名垂青史,要永远在一起,做最快意逍遥的五侠。
江水无声,亿万年来,它听过多少少年誓言?
又见证多少誓言成灰?
我停了桨,任由小舟在巨大的、燃烧般的江面上漂荡。
累了。
忽然觉得,一生都没有这样累过。
我缓缓躺倒在船板上,小小的舟身随波轻晃,像一只温柔的摇篮。
天空是深邃的蓝,落日余晖给它镀上最后一道璀璨的金边,然后金色渐褪,星辰开始一颗接一颗地冒出来,越来越密。
真亮啊。
就像那一年,我们躺在甲板上,看到的星空一样亮。
我望着那片星空,眼睛渐渐模糊。
星光荡漾着,融化着,仿佛又倒映出了盈盈的水光。
水光里,人影晃动。
青衫的楚珩提着酒坛走来,笑容爽朗。
柳莺拽着云舒的袖子,指着星空不知在说什么趣事,云舒抿嘴笑着。
沈默坐在一旁,擦拭着他的剑,偶尔抬头看我们一眼,目光温和。
他们都在,那么年轻,那么好。
他们转过头,一齐向我招手,笑容温暖。
我也笑了,努力地、释然地,向着那片星光与水光交融处,伸出手。
这一次,指尖触到的,不再是冰凉的月亮。
只有一片温柔的、永恒的黑暗,悄然合拢。
同类推荐
 肥妻逆袭:顶流影后她又美又飒(林薇苏辰)最新推荐小说_最新免费小说肥妻逆袭:顶流影后她又美又飒林薇苏辰
肥妻逆袭:顶流影后她又美又飒(林薇苏辰)最新推荐小说_最新免费小说肥妻逆袭:顶流影后她又美又飒林薇苏辰
芠悦
 林薇苏辰《肥妻逆袭:顶流影后她又美又飒》最新章节阅读_(肥妻逆袭:顶流影后她又美又飒)全章节免费在线阅读
林薇苏辰《肥妻逆袭:顶流影后她又美又飒》最新章节阅读_(肥妻逆袭:顶流影后她又美又飒)全章节免费在线阅读
芠悦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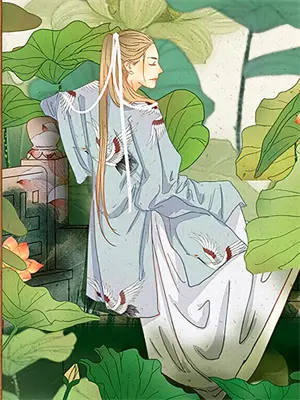 《肥妻逆袭:顶流影后她又美又飒》林薇苏辰完结版阅读_林薇苏辰完结版在线阅读
《肥妻逆袭:顶流影后她又美又飒》林薇苏辰完结版阅读_林薇苏辰完结版在线阅读
芠悦
 肥妻逆袭:顶流影后她又美又飒林薇苏辰新热门小说_免费阅读全文肥妻逆袭:顶流影后她又美又飒林薇苏辰
肥妻逆袭:顶流影后她又美又飒林薇苏辰新热门小说_免费阅读全文肥妻逆袭:顶流影后她又美又飒林薇苏辰
芠悦
 肥妻逆袭:顶流影后她又美又飒(林薇苏辰)全本免费小说_最新章节列表肥妻逆袭:顶流影后她又美又飒(林薇苏辰)
肥妻逆袭:顶流影后她又美又飒(林薇苏辰)全本免费小说_最新章节列表肥妻逆袭:顶流影后她又美又飒(林薇苏辰)
芠悦
 肥妻逆袭:顶流影后她又美又飒林薇苏辰推荐完结小说_热门小说在线阅读肥妻逆袭:顶流影后她又美又飒(林薇苏辰)
肥妻逆袭:顶流影后她又美又飒林薇苏辰推荐完结小说_热门小说在线阅读肥妻逆袭:顶流影后她又美又飒(林薇苏辰)
芠悦
 穿越80之肥妞咸鱼大大翻身(李萍周正泽)热门的小说_热门网络小说推荐穿越80之肥妞咸鱼大大翻身(李萍周正泽)
穿越80之肥妞咸鱼大大翻身(李萍周正泽)热门的小说_热门网络小说推荐穿越80之肥妞咸鱼大大翻身(李萍周正泽)
风平浪静的下午
 李萍周正泽(穿越80之肥妞咸鱼大大翻身)最新章节在线阅读_李萍周正泽全章节阅读
李萍周正泽(穿越80之肥妞咸鱼大大翻身)最新章节在线阅读_李萍周正泽全章节阅读
风平浪静的下午
 穿越80之肥妞咸鱼大大翻身李萍周正泽最新推荐小说_完结版小说推荐穿越80之肥妞咸鱼大大翻身李萍周正泽
穿越80之肥妞咸鱼大大翻身李萍周正泽最新推荐小说_完结版小说推荐穿越80之肥妞咸鱼大大翻身李萍周正泽
风平浪静的下午
 穿越80之肥妞咸鱼大大翻身李萍周正泽新热门小说_免费阅读全文穿越80之肥妞咸鱼大大翻身李萍周正泽
穿越80之肥妞咸鱼大大翻身李萍周正泽新热门小说_免费阅读全文穿越80之肥妞咸鱼大大翻身李萍周正泽
风平浪静的下午







